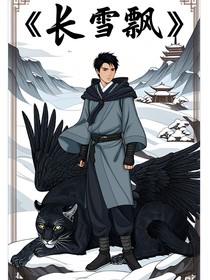第二十回 大渡河悲歌成绝响,太平洋星火启新章(八) (2-1)
何永志轻抚婴儿襁褓,指尖在那绣着“定基”二字的暗纹处停留片刻,沉声道:“此名既随翼王兵败,便不宜再用。当另择新名,以避祸端。”
老汉搓着粗糙的手掌,摇头叹道:“老汉姓胡,祖上三代都是粗人,哪会取什么文雅名字。恩公学问好,还是您给取个名吧。”
陆芸凝视着熟睡的婴儿,忽见一缕晨光透过窗棂,正落在孩子眉心。她轻声道:“不若唤作‘永活’如何?既暗合这孩子命途多舛却顽强存活,又...”她顿了顿,将“永续太平血脉”半句咽了回去。
老妇人突然抱紧婴儿,客家话脱口而出:“胡永活,好!比胡阿狗强百倍!”她粗糙的拇指抚过孩子脸颊,一滴泪砸在“定基”二字上,晕开了陈年的金线。
三人将胡永活郑重托付给胡家后离去。东归路上,他们沿途打听,得知翼王被押解成都受刑,便迅速赶往成都。
到成都城外,他们像往常一样,何永志以金发头套假扮洋商,陆芸作汉人妻子,振华则扮作混血孩童。抬头望去,城门处残缺的尸首在风中轻晃,二人心中不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入城后,二人行走在大街上,来到最热闹的茶馆处。
“啪!”
醒木砸裂了茶桌一角,满堂茶客却见怪不怪——这位被称作“唐疯子”的说书人,早因妄议朝政被革了秀才功名。
“列位看官!”他忽然跳上条凳,破扇子指向虚空,“那石逆戴着八十斤重镣跪在刑台,竟震得地面嗡嗡响!”他故意压低声音:“监斩的骆秉章问‘尔还有何言’,诸位猜那翼王怎生应答?”
何永志用带着古怪腔调的官话高声问道:“What?”随后三人走进茶馆。
唐疯子猛地扯开衣襟,露出胸膛上溃烂的“天”字烙印:“石逆大笑三声,说——”他突然恢复清明嗓音,字字铿锵:“‘自金田起义,所杀清妖何止百万,今日一死,快哉快哉!’”
衙役冲进来时,唐疯子被按在地上仍嘶吼着:“第一百零三刀时他还念诗——”铁尺砸在嘴上,血沫里飞出几个零碎的音节,依稀是“大江”二字。
衙役提着铁尺喝散茶客,目光扫到何永志的金发时却犹豫了。为首的班头啐了口唾沫,到底没敢招惹“洋大人”。何永志顺势揽住妻儿,用蹩脚的官话嚷着:“Go!回领事馆去!”靴跟故意踩过唐疯子吐在地上的血痰。
三更时分,城墙上的火把明明灭灭。何永志贴着墙根阴影游走,断剑在砖缝间轻点三下,人已翻上城楼。守兵正打着哈欠,忽觉颈后微风拂过,便软绵绵瘫倒在地。
残缺的尸首悬在铁链上,断剑划过,铁链应声而断。尸首坠下的瞬间,陆芸在城下张开准备好的麻布,血迹在月白布料上晕开,像极了那年永安突围时撕裂的军旗。
乱葬岗的泥土潮湿阴冷。陆芸以断剑掘坑,何永志沉默地将尸首放入。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垒了个低矮到几乎与荒地无异的土包。
三人静立片刻,对着土包深深一拜。远处犬吠渐近,他们转身离去,再未回头。晨雾中,唯有那株新插的柳枝微微摇曳,柳叶扫过遗落在地的金发头套,沾湿了残余的几缕金丝。
数月后,深秋的广州,外城西北角,越秀山脚下,何振华蹲在老榕树下,小脸皱成一团——蚂蚁们正分成两路:一队扛着虫卵向墙缝迁徙,另一队却固执地往相反方向的树洞搬运碎叶。孩子折了根草茎,轻轻搭在两队蚂蚁之间:“这边才是新家呀...”
秋风卷着落叶拍打窗棂,茶馆里回荡着瓷器轻碰的脆响。陆芸正将一套青花茶具用旧棉袄仔细裹好,何永志掂了掂沉甸甸的包袱,打趣道:“不如把这茶馆整个装船带走?”
太平侠客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陨铜怪力
- (无重生,无系统,单女主,传统修仙)陨铜,神之物,其蕴含着无法比拟的强大力量,恶魔迪亚波罗为了夺得此物,联合死神撒旦,冥王哈迪斯发动了判乱,......
- 1.2万字7个月前
- 藏剑山庄之星魂传奇
- 藏剑山庄之星魂传奇仙侠武侠玄幻奇幻奇迹魔幻天幻神魔天武神幻神武仙武幻想幻玄江湖藏剑山庄剑仙传奇灵剑天剑神剑星魂剑传奇凌霄凌天凌风凌寒凌云凌月......
- 1.1万字6个月前
- 道法学院—甜
- 0.8万字6个月前
- 烬染清秋
- **
- 1.1万字5个月前
- 悍刀越T会
- 第一段就写的主角,上学时光和一些生活片段,第二段写出主角的身世,还有主角的爷爷是前期关键人物,黑道腹黑,武侠类小说,希望大家能喜欢-
- 1.8万字5个月前
- 长雪飘(修仙)
-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 1.7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