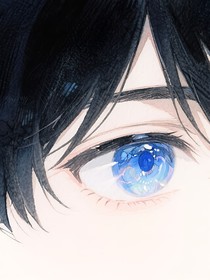第十四章:玉碎情生 (5-1)
晨光透过养心殿的明窗棂斜斜切进来,在金砖地上画出几道明亮的光带。龙涎香和苦腥的药味绞在一起,随着袅袅的热气在光柱里翻滚成絮。萧煜趴在床边浅眠,胳膊压得发麻,后颈的玉枕印出深深的纹路。御案上的更漏"滴答"轻响,比昨夜的雨声更磨人。
"陛下,该换药了。"小禄子捧着黑漆托盘进来,见自家主子趴在床边,明黄常服的袖口沾着干涸的药渍,眼下乌青比床上那位还重。托盘里白瓷碗盛着深褐色的药汁,热气裹着一股说不清的酸苦味直往上冲。
萧煜猛地惊醒,撞上小禄子惊慌的眼神。他直起身时腰骨"咔吧"轻响,这才发现浑身僵硬得像套了副生锈的铠甲。"动静轻点。"他哑着嗓子叮嘱,目光不自觉地飘向床上的人。
谢景澜依旧沉睡,脸色比宣纸上的留白还要浅。太医说要静养,萧煜便命人撤了殿内所有铮亮的铜器,就连平日映得满室生辉的鎏金熏球都换成了素陶的。此刻那人呼吸浅淡,长睫安静垂着,倒比醒时温顺得多——至少不会再用那双看透人心的眼睛盯着他。
"药温正好。"小禄子把瓷碗递过来,碗底垫着块素色绢帕,"太医说这次得慢慢喂,不能像昨夜里那样灌,伤嗓子。"
萧煜接过药碗的手顿了顿。昨夜谢景澜咳得撕心裂肺,暗红的血沫子染透了半条锦被,他急得直接撬开牙关灌药,结果被呛得更凶,温热的血溅在他手背上,像团火似的烧了整夜。
他在床边坐下,小心翼翼扶起谢景澜的肩。触手的体温依旧偏低,隔着层常服能摸到嶙峋的脊背,比想象中还要瘦。萧煜想起去年秋猎,谢景澜策马护在他身侧,玄色骑装勾勒出宽肩窄腰,那时还觉得这权臣身形挺拔如松,原来都是用厚重朝服撑出来的假象。
"张嘴。"萧煜舀了勺药汁送到唇边,声音不由自主放软。昏迷中的人毫无反应,紧抿的薄唇像封死的蚌壳。他想起小时候母妃喂药的法子,伸出拇指轻轻按在谢景澜下唇,稍微使力往里压。
指腹触到温热柔软的唇肉,萧煜心头莫名一跳,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下。谢景澜的唇很薄,平日里紧抿着总显得冷硬,此刻却泛着不正常的淡粉,唇角还沾着未擦净的暗红血痂。
"呃......"谢景澜突然发出声低吟,喉结在苍白的皮肤下滚动了一下。萧煜慌忙收回手,药汁却趁机顺着嘴角淌下去,浸湿了领口的素白中衣。他连忙扯过锦帕去擦,指腹擦过对方滚烫的颈动脉时,谢景澜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腕。
力道不大,带着病弱的虚浮,却攥得很紧。萧煜低头,正对上一双半睁的眼眸。那双眼平日里总是含笑带刺,此刻蒙上了层水汽,像被雨打湿的寒星,失了平日的锐利,却多了几分迷茫的脆弱。
"阿娘......"沙哑的声音从谢景澜喉间溢出,带着浓重的鼻音,"药苦......"
萧煜的心猛地揪紧。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谢景澜——那个权倾朝野、连太后都要忌惮三分的摄政王,此刻竟像个撒娇的孩童。腕间的力道渐渐松了,谢景澜的头歪向他怀里,湿热的呼吸喷在他颈窝,带着浓重的药味。
怀里的人轻得吓人。萧煜僵着身子不敢动,鼻尖蹭到对方微凉的发顶。谢景澜用的是最普通的皂角,没有熏香,此刻混着淡淡的血腥味,竟奇异地不让人反感。他想起五年前那个雪夜,同样是这样一个消瘦的怀抱,隔着冰冷的宫墙和漫天风雪,给了他唯一的暖意。
"陛下?"小禄子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自家主子抱着摄政王的姿势实在太过亲近,明黄常服与石青常服绞在一起,像幅错位的宫廷画。
萧煜迅速回神,猛地推开怀里的人。谢景澜"唔"了一声,又沉沉睡去,只是这次眉头紧锁,像是做了什么噩梦。他慌忙重新舀药,手却抖得厉害,药汁洒在银匙边缘,溅到谢景澜苍白的脸颊上。
"老奴来吧。"小禄子连忙上前。
"不用。"萧煜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沙哑,"朕来。"
龙椅之上,权丞之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九重紫:再嫁英国公
- 酸涩拉扯,甜中小虐的前夫文学鹤发将军宋砚堂X当世名医明玉兰前世,宋墨与明玉兰是父母之命的寻常夫妻,宋墨伊始对满眼都是他的妻子只有相敬如宾之谊......
- 1.3万字7个月前
- 误嫁腹黑王爷:王妃,请上榻
- 天辰国,风华二十三年。花澄被皇上赐婚给阮云霆王爷,然而她心有所属,不愿听从父母之命嫁给一个陌生人。为此与父母发生激烈冲突,坚决抗婚。尽管王爷......
- 5.9万字7个月前
- 玄田萌宝:福佑苍生
- 6.2万字6个月前
- 千山与你同见
- 简介正在更新
- 0.7万字6个月前
- 重生之恶妃逆袭韶华珑
- 死后重生归来
- 2.3万字6个月前
- 男公子
- 不想说
- 0.9万字6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