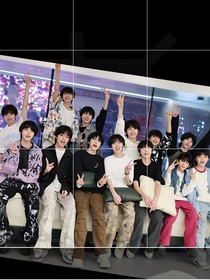第44章:老砖家谱与槐树下的承诺 (2-1)
整理老砖档案的日子,是从一叠泛黄的旧图纸开始的。沈星辞把工作室的书架腾出半层,堆满了从档案馆借来的资料——民国时期的学堂平面图、抗战时的医院布告、甚至还有五十年代居民搬入时的登记册。
陆野则搬来了一箱子修复记录,厚厚的笔记本上画满了砖纹草图,每块有特殊印记的老砖都标着编号和发现地点。“这块带弹痕的是在西墙根挖的,”他指着一张照片给沈星辞看,“张师傅说像是当年打仗时留下的,砖缝里还嵌着小弹片。”
沈星辞把照片贴进档案册,在旁边写下:“民国二十七年,此处为临时医院,砖块见证战火与救治。”笔尖划过纸面时,陆野正低头给砖片标本贴标签,阳光从窗缝漏进来,在他发梢镀了层金边,连带着空气里的灰尘都变得慢悠悠的。
“你看这个。”沈星辞忽然指着登记册笑起来,“一九五三年,有户姓陆的人家搬来住,登记人写的是‘陆守义’,是不是你爷爷?”
陆野凑过来看,手指点着那行字:“还真是!我爷爷说过他小时候在这附近住,没想到真能找到记录。”他忽然眼睛一亮,“说不定咱们修的砖里,就有他家当年住过的墙呢?”
这话像颗小石子投进心湖,沈星辞翻档案的手顿了顿。他想起陆野说过,爷爷总念叨老墙的梅花砖“能挡灾”,原来这份牵挂早藏在时光里,绕了一圈又回到他们手里。
整理到深夜时,两人就趴在桌上吃泡面。陆野总把蛋肠夹给沈星辞,自己啃面饼时,目光却黏在他低头写字的侧脸上。“明天去趟老街吧,”他忽然说,“找张师傅他们聊聊,说不定能记起更多细节。”
老街坊们的记忆,是比图纸更生动的档案。张师傅记得学堂的钟楼每天响六遍,王奶奶藏着当年医院发的搪瓷碗,连总在纪念墙前晒太阳的李大爷,都掏出了父亲留下的修墙工具——一把磨得发亮的瓦刀,木柄上刻着模糊的“守”字。
“这瓦刀传三代了,”李大爷摩挲着刀柄,“我爹修学堂的墙用它,我修自家院墙用它,现在你们修老砖,也算续上缘分了。”
陆野接过瓦刀时,掌心被木柄的纹路硌得微微发痒。沈星辞趁机拍下这一幕,照片里,老瓦刀的影子落在档案册上,像给历史盖了个温柔的戳。
档案册渐渐厚起来,每一页都贴着砖片照片、手写记录,还有街坊们的口述录音二维码。沈星辞在封面上写下“老砖家谱”四个字,陆野则找了块小砖刻了枚印章,盖在落款处——还是那熟悉的梅花纹,只是这次旁边多了个小小的“野”字和“辞”字。
“像给老砖办了户口本。”陆野举着档案册笑,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封面上,砖印章的纹路清晰又温暖。
沈星辞忽然想起什么,拉着他往老槐树跑。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雪白的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软绵绵的,空气里飘着清甜的香。
“你看这个。”沈星辞从包里掏出个小盒子,打开后是块打磨光滑的长砖片,上面用激光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从民国学堂的校长,到抗战时的医生,再到修复时的工人和街坊,最后是他和陆野的名字,并排刻在最下方。
“这是‘老砖家谱’的实物版。”沈星辞把砖片立在槐树下,花瓣落在上面,像给名字盖了层雪,“以后把它嵌在纪念墙旁边,这样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是谁让这些老砖重新活了过来。”
陆野蹲在砖片前,指尖一个个划过那些名字,忽然握住沈星辞的手。槐花落在两人交握的手上,他抬头时,眼里的光比阳光还亮:“那咱们的名字,要一直刻在最显眼的地方。”
“不止名字,”沈星辞回握住他,掌心的温度混着槐花的香,“还有以后的日子。”
话音刚落,远处传来林溪的喊声。她举着手机跑过来,屏幕上是文创店的订单页面:“你们的‘老砖家谱’文创火了!好多人留言说要定制刻名字的砖片,还有人问能不能预约参观修复工作室呢。”
陆野和沈星辞对视一笑,眼里的默契像老砖的纹路,早已刻入心底。
逆途恋梦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静野回望
- 喧闹的音乐,碰撞的酒杯,嬉笑的言语……稍不留神间,悄然潜入的物质勾起寻欢的本能,蚕食空荡的欲望。间奏激昂,一曲终了,盛大的舞台上,只留微笑的......
- 1.3万字7个月前
- 王者荣耀:与你岁岁年年
- 王者CP,乱磕,he
- 9.5万字7个月前
- 凹凸世界:吾为冥珲
- 小学生文笔,本人赞德吹,另一人紫堂真吹,因为要上学所以可能更新慢,私设,轻喷,想看什么可以评论,赞德梦女和(另一人)紫堂真梦女,有合写人啦本......
- 2.3万字6个月前
- TF四代:这是我青梅!!!
- 包括汪浚熙
- 0.2万字6个月前
- TOP:废柴七小姐误入男校
- 【女扮男装/小甜饼/强制爱】要素过多,玛丽苏预警,注意避雷⚠️星际司令官家的七小姐是脑力体力全废,是公认的“宇宙废柴”,然而虽然“废”!却是......
- 7.0万字4个月前
- 花千骨之笙萧曦环
- 曦沐瑶:“玲珑骰子生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笙箫默:“曦儿,我不想再做你的师父了,我想……做你的夫君,你……愿意吗?”曦沐瑶:“我愿意”曦沐瑶......
- 30.8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