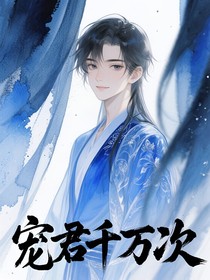上元灯影·惊鸿 (5-1)
永安二十三年的上元灯节,京城朱雀街被灯笼照得像条淌着光的河。朱红宫灯悬在飞檐下,琉璃灯串垂在巷陌间,连护城河边的柳树上都缠满了绢灯,风一吹,万千光点晃得人眼晕。空气中浮动着糖画的甜香、煮茶汤的醇厚、孩童手里糖葫芦的酸气,混着远处戏楼飘来的弦乐,织成一张热热闹闹的网,将整个京城裹在其中。
元止墨勒住缰绳时,胯下的“踏雪”刚从围场的旷野奔进这人间烟火地。马鼻里还喷着带着枯草气息的白汽,骤然被满街的喧嚣裹住,不安地刨了刨蹄子。他偏过头,看身后的内侍福安捧着件狐裘披风小跑追赶,帽檐上沾着的围场雪渣还没化,在灯笼光下闪着碎银似的光,忍不住嗤笑一声。
“殿下!慢些!”福安跑得气喘吁吁,袍子下摆扫过青石板,带起一串细碎的声响,“夜里风凉,仔细冻着——”
“冻着?”元止墨反手接过披风,却没往身上披,只随意搭在马鞍前桥,玄色骑装的袖口被风掀起,露出腕上磨得发亮的银镯子——那是母妃给他求的平安符。“本王在围场能赤膊斗熊,这点风算什么?”他说着,故意夹了夹马腹,踏雪立刻扬起前蹄,惊得路边几个提着兔子灯的孩童尖叫着躲闪。他哈哈大笑起来,少年人的野气比头顶的灯笼还要亮,袖袋里揣着的太傅戒尺硌着腰侧,像块调皮的石头。
十三岁的年纪,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仗着元景宴帝的偏爱,他在京城里向来横着走——前几日嫌礼部尚书奏对时啰嗦,趁人转身的功夫,把人家乌纱帽扔进了护城河里,气得老尚书在金銮殿上哭着要辞官;昨日太傅教他读《资治通鉴》,他嫌字太密像蚂蚁,竟把先生的紫檀戒尺偷揣进袖袋,此刻那冰凉的木头还在跟他的腰侧较劲。
“前面是灯谜棚!”随从兴奋地指着前方,那里攒动的人影比别处更密,“听说今年的头奖是支羊脂玉簪,雕了满工的缠枝莲!”
元止墨正想催马过去,街角突然窜出一辆青帷马车。赶车的小厮约莫十五六岁,脸上还带着未脱的稚气,显然没料到会撞见疾驰的骏马,吓得手一松,缰绳在手里缠成了乱麻。踏雪被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惊得人立而起,前蹄几乎要踏上车顶的铜铃,清脆的铃声混着马嘶,在喧闹的街面上撕开一道口子。
“放肆!”护卫统领拔刀出鞘,寒光映着灯笼的红光,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影子,“给我拿下这刁民!”
“住手。”元止墨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他稳稳坐于鞍上,左手紧扣马鬃,右手已抽出腰间的马鞭,鞭梢在空中划出道残影,却没有挥下去。目光越过躁动的马颈,落在被风掀起的车帘一角——
那一瞬间,周遭的喧嚣仿佛都被按下了静音。
车里坐着位少女。
她穿件月白绫袄,领口袖缘绣着细碎的缠枝纹,针脚密得像春雨织的网,在灯笼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许是被惊马吓着,她正抬手按着被风吹乱的鬓发,皓腕抬起时,露出半截羊脂玉镯,莹白得与衣袖几乎分不清。烛光从车窗的缝隙漏进去,在她脸颊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衬得肤色莹白如瓷,连耳后那点柔软的绒毛都看得清晰。唇瓣没涂胭脂,透着点病气的淡粉,像早春刚绽的桃花瓣,沾着未干的露水。
最惹眼的是那双眼睛。
睫毛长得像蝶翼,此刻正簌簌地颤,显然含着惊惶。可眼底却清明得很,像盛着一汪刚融的雪水,映着窗外的灯笼,亮得能照见人影。那目光扫过他时,没有寻常闺阁女子的怯懦,甚至没有半分谄媚,只有一闪而过的审视,像小鹿撞见了猎人,却没忘了抬头看清对方的模样。
墨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仅此一人
- 栾易和祁杨遇见的那一刻起就只有这一人了,明明是那么好,却因为世俗的眼光而分开,祁杨讨厌那些人,临齐门不是以前的家了,他好恨,他也好想师尊。不......
- 0.4万字6个月前
- 落荷
- 跟芙蓉同名的一个女生,穿越到他身上,暴打渣男贱女,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看她如何做
- 0.8万字6个月前
- 魔法大陆传奇
- 在神秘大陆,黑暗势力妄图抢夺宝物、摧毁和平。苏逸持神器融合净化之力,与九尾狐白璃、觉醒仙族血脉的逸尘及学院学生并肩作战。他们在冒险中历经磨难......
- 19.0万字6个月前
- 十世狐妖
- 万人迷多男主修罗场,大女主玉卿卿是一只白孤狸精,性格乖张肆意,在琳琅神君闭关期间,偷偷潜入闭关之地欲窥视传闻三界第一美男琳琅神君,不想打扰神......
- 32.3万字2周前
- 惟乐
- 废话不多说,直接开看
- 1.2万字2周前
- 宠君千万次
- 雪地相逢,从暗夜修罗堡寻宝开始结缘。»»»云藏时x弦染,弦染追的云藏时。弦染是高维度种族,可男可女。TA要摘取最甜美的果实。主角是高纬度星际......
- 4.0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