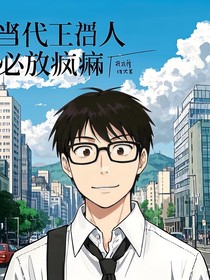月满与针脚 (2-1)
白露的月光漫进布庄时,苏晚正在给“中秋长卷”绣最后轮月亮。用的是半透明的真丝绡,针脚密得像撒了把碎银,远看倒像月光自己落在了布上。
“念念说要在月亮里绣只兔子,”陈砚帮她扶着绣绷,指尖避开绡面的针脚,“刚才画了张草图,兔子手里还抱着个小绣绷。”他把草图铺在旁边,纸上的兔子耳朵歪歪扭扭,倒和念念去年绣坏的荷包上那只重合。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月光信箱”来了。他们用竹篾编了个半开的圆筐,像轮没满月,内壁糊着苏晚染的月白色棉布,让来的人把想对老手艺说的话写在纸上,塞进筐里。“我们会把这些话绣成月光纹样,”年轻人指着筐底的空白,“满月那天挂在布庄的梧桐树上,让月亮照着这些针脚。”
苏晚取来银丝,在信箱的竹篾缝隙间绣了圈云纹。针脚松松垮垮的,风一吹能晃出细碎的光。“话得透气,”她穿针时说,“就像小时候对着月亮说话,说完了,心事就跟着云飘走了。”
陈砚在每张信纸的抬头画了个小月亮,有的缺个角,有的带着云影,有张画得格外圆,旁边注着:“这是念念说的‘兔子藏在里面’的月亮。”他把信纸折成纸船的样子,“纸船能漂,让话顺着月光漂到该去的地方。”
秋分那天,来投信的人排到了巷口。补伞的老师傅写:“想再修把油纸伞,让伞骨的声音陪着过冬天”;学书法的学生画了支毛笔,笔锋缠着绣线;连刚会写字的小孩都歪歪扭扭地写:“我奶奶绣的鞋垫,比太阳还暖”。
念念把自己的信叠成小兔子,塞进信箱最深处。信上画了三个手拉手的小人,头顶有轮满月,旁边用拼音写着:“要一直在一起”。她踮着脚对苏晚说:“兔子会把话带给月亮的,月亮记性好。”
中秋前夜,他们把信取出来,在院子里摆了长桌。苏晚和学生们挑出最动人的句子,用不同的线绣在月白布上:“暖”字用橘色丝线,针脚密得发烫;“伞”字缀着银丝,像雨滴落在伞面;“在一起”三个字用了三色线,红的、蓝的、黄的,缠成小小的麻花。
陈砚在布的边缘画了圈梧桐叶,叶尖都朝着月亮的方向。“叶子会引着光,”他给叶筋描墨时说,“就像回春巷的石板路,总能把人带回家。”
满月升起时,绣满字的白布被挂在了梧桐树上。银丝的云纹在月光下闪着光,针脚里的字像活了过来——“暖”字的橘色融在月光里,竟透出点夕阳的红;“伞”字的银丝晃啊晃,像真有雨滴在跳。
有位老太太摸着“鞋垫”两个字,忽然抹起眼泪:“这针脚,跟我老伴当年帮我穿的线一个样。”她从兜里掏出片压平的桂花,塞进信箱的缝隙,“给月亮捎点香。”
夜深了,布庄的灯还亮着。苏晚在新做的月饼盒上绣了只兔子,兔子手里的绣绷上,留着半针没绣完的线。陈砚把没绣完的信折成纸飞机,往窗外一扔,飞机穿过月光,落在梧桐树下的“月光信箱”旁。
“剩下的针脚,”他给苏晚倒了杯桂花酒,“等明年月亮圆时再补。”
念念趴在窗边看月亮,忽然指着树影说:“兔子出来了!它在啃‘暖’字的针脚呢。”苏晚走过去,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月光穿过梧桐叶的缝隙,落在布上的针脚,倒真像只兔子的轮廓在动。
檐下的风铃换了新的铜片,上面錾着小小的月亮。风吹过时,声音混着远处的虫鸣,像谁在用月光当线,把满巷的故事串成了串。
苏晚低头继续绣兔子的耳朵,针尖穿过布面时,忽然觉得这动作熟悉得像上辈子就做过——就像每年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可落在布庄的光,总带着同样的温度。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当代正常人绝不发疯实录
- 林晓,一个被生活反复摩擦的社畜,坚信自己是个无比正常的普通人。然而,他的生活却被奇葩同事、神经质邻居和戏精家人围得水泄不通。客户的刁难让他抓......
- 4.5万字7个月前
- 夜雾之中
- 这个跟游戏内容差不多吧,以通关为主
- 0.2万字6个月前
- 北边的你
- 注意本文是原创本文是原创本文是原创重要的事说三遍,还要文中重要的角色或引入后续剧情的才会细介绍,不喜勿喷,谢谢
- 1.0万字6个月前
- 心理学大全
- 介绍心理学,小红书搜(樵君吖)
- 5.2万字6个月前
- 樊振东:追逐我的星光
- 同人文,不上升现生!!!青梅竹马许念卿×樊振东平行线总会在特定的情况下相交
- 6.3万字2周前
- 穿越之扭转炮灰白月光人生
- 【单男主+发疯+白月光文学+不带脑甜宠文】林沅穿越进一本古早言情小说中的作死白月光后发现为什么故事情节根本不一样?不是说好了作死白月光,为什......
- 0.4万字3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