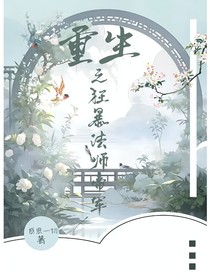观建宁战报书
(养心殿·丑时)
烛火在铜鹤灯盏里跳,将战报上的墨迹照得发颤。我捻起那页纸,边角已被驿卒的汗浸得发皱,"邹军三十万围建宁,首日未破"这行字,墨浓如铁,似要透纸而出。
案头堆着七封急报,最上面那封盖着杨烈的私印,是昨夜三更到的。我用银簪挑开蜡封,信纸带着北地的土腥气,杨烈的字向来刚硬,此刻却在"柳承宗掘深沟阻地道"处洇了个墨团——想来是写时心绪不宁。
"陛下,三更了,要不要传些莲子羹?"内侍李德全的声音从帘外飘进来,带着小心翼翼的颤。
"不必。"我扬手让他退下,指尖抚过战报上的城防图。杨烈画得细,连城根的每处箭垛都标了,西瓮城那道红圈尤其扎眼,旁边注着"守卒多为新募,甲胄不全"。这老东西,总爱把胜算藏在细节里。
第二封是秦岳的密报,用的是军中暗语。"穴地至十丈,闻城根有掘土声",我对着译本校,"闻"字被圈了又圈——他是在说柳承宗已有防备。忽然想起去年秦岳在河西打突厥,也是这样用暗语传信,那时他在信尾画了只小狼,说"已断其喉",如今这信上却只有光秃秃的城图。
窗外起了风,卷着秋雨打在窗纱上,像极了建宁城下的鼓点。我取过顾长风的战报,他倒是直白,"佯攻三门,守卒未乱,柳承宗亲登城楼",末尾加了句"陈军炊火较昨日少三成"。这小子,打小就爱记这些旁门左道,如今倒成了大用。
最底下压着封细作的密信,是用明矾水写的,我对着烛火烘了半刻,字迹才显出来:"建宁粮道被断,柳承宗斩粮官以安军心"。墨迹浅淡,想来是在暗处匆匆写就。我忽然想起三年前伐北齐,也是这样的细作信,说齐主在宫内宴饮,三日不朝——那时的战报,可比现在热闹多了。
"李德全。"我扬声,"取舆图来。"
李德全捧着牛皮舆图进来,图上的江河用青线标着,建康城的位置被朱砂点了个圈。我用手指量着建康到建宁的距离,指尖在"采石矶"处顿住——那里是柳承宗的老巢,当年他以千人拒我军三万,如今却困在城里,倒像是命运的轮回。
杨烈的战报里说"已筑土台五座,高过城堞",我想起去年在龙门关看他练兵,他指着投石机说"攻城不用蛮力,要让守城的人先怕"。如今想来,那些土台,怕不只是为了观敌,更是要让建宁的守军,日夜看着城外的黑压压一片,先自乱了阵脚。
案头的铜漏滴答响,已过四更。我将七封战报按日期排好,忽然发现杨烈的信里,五处提到"气"字。"三军鼓勇""敌气渐泄",最末一句是"臣已悬千金募死士,士气可用"。这老东西,打了一辈子仗,还是信那句"气可鼓不可泄"。
风卷着雨丝扑在窗上,我看着舆图上的建宁城,忽然觉得它像颗被攥在掌心的珠子,柳承宗是那层硬壳,而杨烈,正用耐心磨着这壳。磨得久了,壳总会裂的。
"李德全,"我将战报收拢,用玉镇纸压住,"明日早朝,告诉兵部,给建宁前线送些棉衣,北地该冷了。"
李德全应着,却不走,只盯着我鬓角的白发。我笑道:"看什么?朕还能等得起。"
他退下后,殿里只剩烛火和漏声。我拿起杨烈的战报,在"两月可破"那行字上,轻轻画了个圈。建宁的秋,该比长安冷些,但愿那些土台上的士卒,能多撑几日——等破了城,朕自会给他们庆功
大邹高祖武皇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千山夜雪
- 简介正在更新
- 1.0万字7个月前
- 如愿:盛世
- 自幼天赋绝佳的道士只因手刃了杀了至亲的仇人,却遭天雷,受世人唾骂,年少时相遇的女子,是家世显赫的敌国将军。为了盛世,多少少年流干了血,朝中的......
- 4.2万字6个月前
- 重土异梦
- 无脑爽文党慎入白切黑“反派”谢安宿x暴躁心机“降刑者”任怀远原以为尽在掌握,不料只是缓兵之计。究竟谁是谁的棋子?强强对立还是强强联手?
- 2.5万字6个月前
- 重生之狂暴法师帝君
- 东华帝君重生到2005年奇迹游戏开服前两天。他提前进入游戏,获取唯一的狂暴法师职业,在游戏中,他宛如战神,领先其他玩家的等级和战力。新手村野......
- 10.8万字5个月前
- 被放弃的他
- 她说 我玩腻了你,想甩了你,你又能怎样? 他说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不会离开你的。 他说 你是我的全部,虽然我在你心中没......
- 3.9万字2周前
- 太子爷的心尖宝
- “我无法确定人是否真的有下辈子,但我顾时邺今生今世只爱柳婉清一人,永不言弃!”锦禾年间,柳婉清死在了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外人只知,长公主薨后受......
- 2.4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