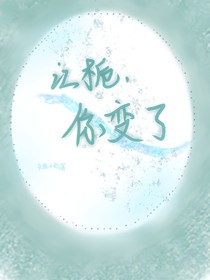灯下谈“论”的破绽与心动 (2-1)
书房的台灯暖黄如蜜,将两人的影子投在书架上,像幅被拉长的剪影画。林曦指尖划过《资本论》的烫金书脊,忽然想起傍晚沈砚抱着一摞经济学论文回来时,眉峰拧成川字的模样。
“卡在哪个部分了?”她转身时,椅腿在地板上蹭出轻响。
沈砚抬眼,镜片后的目光带着点罕见的窘迫。他推过来一张写满批注的A4纸,红笔圈住的“剩余价值”四个字格外扎眼:“总觉得这里的逻辑链……像漏了个扣。”
林曦俯身去看,发尾不经意扫过他手背。沈砚的指尖猛地蜷缩,像被烫到似的,却听见她低笑出声:“沈大律师也有卡壳的时候?”
“术业有专攻。”他清了清嗓子,试图维持镇定,“我更习惯从法律条文推导权利义务,这种宏观理论……”
“其实很好懂。”林曦抽过他的钢笔,在空白处画了个简单的流程图,“就像你接案子,律所收的咨询费里,扣除房租水电和助理工资,剩下的才是你的劳动所得——这部分,就是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
沈砚盯着那个歪歪扭扭的流程图,忽然笑了。不是平日里礼貌性的浅勾唇角,而是眼角眉梢都漾开的笑意,连带着镜片都折射出细碎的光:“这么说,我每天上班,也是在被‘剥削’?”
“理论上是。”林曦仰头时,灯光恰好落在她眼底,亮得像盛了星子,“但马克思更想讨论的是,如何让劳动者拿回属于自己的价值——就像你帮弱势群体打官司时,其实是在矫正这种‘失衡’。”
他忽然沉默了。原来那些被他视作“专业本能”的事,在她眼里竟有另一层意义。书房里只剩下窗外的蝉鸣,和她翻书时纸张摩擦的轻响。沈砚看着她指尖在书页上跳跃,忽然注意到她指甲修剪得圆润干净,虎口处有淡淡的薄茧——是常年握笔留下的痕迹。
“高中时写作业,也这么用力?”他鬼使神差地问。
林曦的动作顿了顿。她想起高中图书馆的旧木桌,自己总在沈砚斜后方的位置,笔尖在草稿纸上洇出深深的墨痕,只为让他抬头时,能不经意瞥见她的“认真”。那时的她像只胆小的寄居蟹,把所有心事都藏在书本筑起的硬壳里。
“大概是怕写得太轻,连自己都看不清吧。”她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沈砚的心猛地一缩。他想起前几天从同桌那里听到的话——高中班主任总在办公室说,“没爹妈管的孩子,心思就是不放在正途上”。原来那些被他忽略的岁月里,她是这样小心翼翼地,用笔墨为自己搭建避难所。
“那本古诗词抄本,”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发紧,“当年被没收时,是不是很疼?”
林曦握笔的手颤了一下。墨水在纸上晕开个小墨点,像朵突然绽放的墨花。她没想到他会突然提起这个,眼眶瞬间就热了。那本抄满纳兰词的笔记本,是她偷偷攒了三个月早饭钱买的,被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撕成碎片时,她甚至不敢掉一滴眼泪。
“还好。”她吸了吸鼻子,试图扯出个笑,“后来发现,比起诗词里的风花雪月,马克思的理论更能让人站稳脚跟。”
沈砚伸手时,才发现自己的指尖在抖。他原本想像电视剧里那样拍拍她的肩,最终却只是轻轻碰了碰她手边的钢笔:“以后想看什么书,告诉我。不管是《资本论》还是纳兰词,都不会再有人能没收。”
这句话像颗投入深湖的石子,在林曦心里漾开层层涟漪。她低头盯着那支钢笔,忽然想起傍晚他回来时,衬衫袖口沾着点墨渍——想必是翻她那些批注笔记时蹭到的。这个总把“理性”挂在嘴边的人,原来也会偷偷做这么多笨拙的事。
台灯的光晕里,两人之间的距离忽然变得很近。她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松味,混着旧书页的油墨香;他能看见她睫毛上沾的细小灰尘,像停着只透明的蝶。
“沈砚,”林曦忽然抬头,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颤抖,“你是不是……”
沈先生,香菜要挑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黎桐:威雨绸缪
- 夜巴黎收了一位新的女徒弟,叫雨桐,自带85万粉丝,多才多艺,一次恋爱没谈过,是溜溜的亲妹妹,后与王威成为cp
- 0.9万字6个月前
- 这条路我来走
- 妹妹如何在哥哥的陪伴下成为凤凰
- 2.1万字6个月前
- 城南的夏天
- 0.9万字5个月前
- 他的麦杆菊
- 大家我回来了,因为一些原因我停更和终止精修了,经过这一年的思考构思,我打算重新写,名字还是这个但是主角和内容会和以前不一样,请见谅,这本书的......
- 2.9万字5个月前
- 江栀,你变了
- “你变了,你当初可不是这个样子的!”“讨厌你”“为什么?”“因为时言知!”“明明是你变了,为什么你心知肚明,你还来问我?你回头看过我吗?看过......
- 2.3万字3周前
- 哥们,感觉有点虐啊
- 清冷腹黑学霸弟弟和温柔的哥哥,甚至还有一个突然而来的学神,watermelon?什么什么?还有这种好事,这个老弟和这个sunny不一般,不仅......
- 8.1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