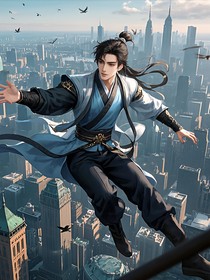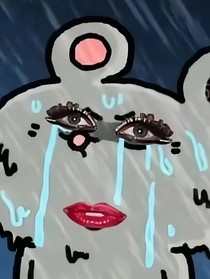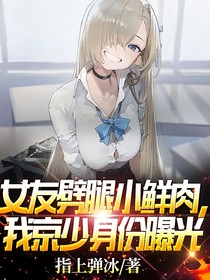第36章 银杏黄时是归期 (2-1)
霜降过后,后山的银杏叶总算染透了黄,像把阳光揉碎了铺在枝桠间。林砚舟揣着那本敦煌日记出门时,苏晚已推着辆旧自行车等在巷口,车后座绑着个竹篮,里面放着块蓝布、两盏热茶,还有包沈玉衡生前最爱的桂花糕。
“林先生,我问了老周头,他说后山那两棵银杏就在半山腰,顺着石阶走半个时辰就到。”苏晚把车把往他那边递了递,“您要是走不动,咱们就骑车到山脚下,再慢慢往上挪。”
林砚舟望着车把上磨得发亮的木纹,忽然想起二十年前,沈玉衡也是骑着这么一辆二八大杠,载着他去城郊看银杏。那时沈玉衡的后背还挺直,穿过风时会回头喊:“砚舟,抓紧了,咱们赶在日落前到!”如今风还是那样的风,只是骑车的人换了模样。
“不用,”他攥紧了手里的日记,指腹蹭过封面上的折痕,“我想自己走上去,陪他慢慢走。”
石阶是近年新修的,却也铺着层薄霜,踩上去咯吱响。苏晚跟在他身后半步远,见他每走几步就扶着树干歇一歇,额角沁出细汗,却没敢多劝——她知道,有些路,林砚舟得自己走,就像有些约定,得他亲手来赴。
走到半山腰时,风忽然转了向,卷着几片银杏叶落在林砚舟肩头。他抬头望去,两棵银杏树就立在不远处的平地上,树干粗得要两人合抱,金黄的叶子层层叠叠,连地面都铺了层软乎乎的“金毯”。
“到了。”林砚舟声音轻得像被风吹散,他快步走过去,伸手抚上左边那棵树的树干——当年他种这两棵树时,特意在左边这棵的树皮上刻了个小小的“衡”字,如今树皮长粗,字迹被裹在年轮里,只隐约露出个模糊的轮廓。
苏晚把竹篮放在树下的青石上,铺开蓝布,将桂花糕和热茶摆好:“沈教授要是知道您年年都来浇树,肯定高兴。”
林砚舟没应声,他从怀里掏出那本敦煌日记,轻轻放在蓝布中央,又把沈玉衡当年留下的信笺展开,压在日记上。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落在信纸上“待我回来,咱们就去后山种棵银杏树”那行字上,像是给这句话镀了层暖光。
“玉衡,”他蹲下身,指尖轻轻敲了敲日记封面,“我带桂花糕来了,你以前总说,这糕甜而不腻,配着热茶正好。你看这两棵树,长得比我还高了,今年的叶子黄得早,我猜你是等不及,要催我来赴约了。”
风又吹过,银杏叶簌簌落下,有片正好落在日记上,像只金黄的手,轻轻按在“砚舟,勿念”那四个字上。苏晚忽然看见林砚舟的肩膀不再颤抖,他嘴角牵着点笑意,眼里虽有湿意,却没了往日的沉郁。
“那年你走后,我把《壁画修复札记》校改完了,送去出版社时,编辑说这是近年最好的修复著作。”林砚舟絮絮地说着,像在跟老朋友聊天,“前阵子苏晚帮我整理书房,翻出你当年画的敦煌飞天草图,我照着改了幅长卷,下个月要在市美术馆展出,名字就叫《归期》。”
苏晚忽然指着树影里的石阶,轻声说:“林先生,您看那。”
林砚舟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石阶尽头的光影里,似乎站着个熟悉的身影——藏青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揣着本札记,正朝着这边笑。他猛地站起身,心跳得发紧,刚要迈步,那身影却被风吹散,只剩几片银杏叶悠悠飘落。
“是我眼花了。”林砚舟失笑,却没觉得失落,他蹲回蓝布旁,拿起块桂花糕,掰成两半,一半放在日记旁,一半塞进嘴里。甜香漫开时,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秋天,沈玉衡也是这样,把桂花糕掰成两半,塞给还在临摹壁画的他:“砚舟,先吃口甜的,不然眼睛该酸了。”
“味道没变,”林砚舟对着银杏树轻声说,“就是我牙口不如从前了,你要是在,肯定又要笑我。”
断绝关系后,她们悔不当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都市修仙:我在游戏里成仙了
- 在现代都市的喧嚣中,林轩是一个普通的游戏玩家,生活平凡、毫无波澜。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事件,让他获得了可以在现实世界和虚拟游戏中双重修炼......
- 22.2万字10个月前
- 回忆之书:我的故事
- 关于男主的经历。最后再改编一下,一生的经历。还有一些其他角色的故事,刑侦故事什么的。
- 8.0万字10个月前
- 江烟
- 2.1万字10个月前
- 又被弟弟看上了
- 为维护本站良好的小说创作环境,您作品《交通发达弟弟变p友,求解决两人在见面的第一眼夏林觉警笛大作“坏了要争家产”第二面夏林觉心下一惊“坏了,......
- 0.5万字9个月前
- 财权之巅
- 官二+神豪+打脸+校花+反派+爽文
- 59.6万字9个月前
- 分手后,我穿进二次元
- 你萧清宇是个窝囊废,渣男、混蛋,打牌、脏话、欺负女朋友、无所不能。可是,如同往常的一天,萧清宇的女朋友和他提了分手,她走后,萧清宇昏沉地走进......
- 4.1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