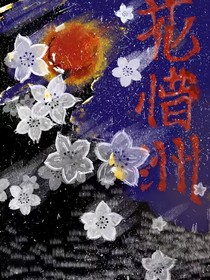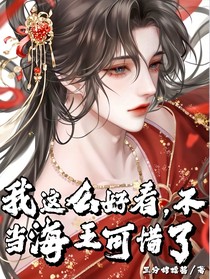第二十六章 菊棠同绣话余温
绣娘祠的晨雾还没散,柳眉就把母亲的绣谱摊在供桌上,用干净的布轻轻擦拭着封面的灰尘。谱子上的黑菊暗纹经过十年,颜色虽淡,却在晨光里透着一股释然——就像那些被揭开的旧案,终于不用再藏在阴影里。
“柳眉姐,这谱子上的菊,要不要绣在新帕子上?”林丫拿着针线走过来,针尖穿着淡黄色的丝线,“上官姐姐说,要把菊和海棠绣在一起,记着这次的案子。”
柳眉点头,接过丝线:“绣吧,不过这菊要绣得淡些,衬着海棠的暖,就像真相总在善意里显形。”
上官柠黎走进来时,正看到两人凑在绣绷前穿针引线。沈兰在一旁调染料,淡粉的海棠色和浅黄的菊色在碗里晕开,像把晨雾揉进了染料里。“今天的染料,加了晒干的秋菊瓣,颜色更柔。”沈兰笑着说,“等绣好了帕子,给漕运码头的张婶送几块,她上次受了惊,正好用暖帕子压惊。”
正说着,赵老栓和赵绣娘来了,手里拎着一篮刚蒸好的海棠糕,糕上印着小小的“安澜”二字。“这是用河堤边新收的海棠果做的,”赵绣娘把糕放在桌上,“给大家尝尝,也算是给这次结案添个喜。”
李三郎闻着香味跑进来,抓起一块糕就咬:“好吃!比城里糕点铺的还香!下次说书先生讲黑菊案,我就说咱们查完案还吃了海棠糕,让故事更热闹!”
众人都笑了,祠堂里的笑声混着丝线的簌簌声,把秋晨的凉意都驱散了。上官柠黎拿起一块糕,咬下一口,甜香里带着点菊的清苦——就像这案子,虽有惊险,却终有回甘。
午后,苏明远来送结案文书,说王三因贪墨、绑架等罪被判流放,漕帮的私盐网络也被彻底捣毁,朝廷还下了令,要重修漕运码头的监管制度。“这文书里,特意提了绣娘祠的功劳,”苏明远笑着说,“以后百姓说起漕运案,都会记得是绣娘们的针脚和大家的坚持,才揭开了真相。”
柳眉接过文书,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盖着大理寺的红印,旁边还画着一朵小小的海棠菊。“这是我让画工加的,”苏明远说,“记着菊棠同开,善恶分明。”
夕阳西下时,大家把绣好的“菊棠帕”分发给百姓。漕运码头的张婶接过帕子,摸着上面的针脚,眼眶红了:“多谢姑娘们,这帕子暖,心里也暖。”孩子们戴着帕子在码头跑,淡粉和浅黄的影子在地上晃,像撒了一地的阳光。
回到祠堂,上官柠黎把结案文书和“菊棠帕”一起放在供桌上,和之前的案卷、绣活摆在一起。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丝帕上,海棠和秋菊的针脚在光里格外清晰。
“姑娘,下次再办案,咱们还绣新的花吗?”李三郎靠在门边,手里把玩着木雕小伞。
上官柠黎看着丝帕,笑着点头:“当然。要是遇到梅案,就绣梅;遇到兰案,就绣兰。不过不管绣什么,都要衬着海棠,记着咱们查案的初心——不是为了定罪,是为了让大家能安稳地绣一朵花,吃一块糕,过踏实的日子。”
夜风拂过祠堂,供桌上的文书轻轻翻动,丝帕上的菊棠在月光下静静相依。上官柠黎的油纸伞靠在门边,伞面上的海棠花,仿佛也映上了一点菊的浅黄——就像这京城的故事,总在新案与旧影里流转,却永远藏着一份暖人的余温,等着被针线绣进寻常日子里,等着被油纸伞护着,一直走下去。
上官柠黎查诡案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让你救黛玉,没让你花式宠妻上天
- 一周穿越恢复前世记忆的薜蟠,直接被莫名其妙的力量拉扯到远隔万里之远的林黛玉识海中。机缘巧合之下解救了即将被前世的怨气。结合痴男怨女的情状迫害......
- 5.7万字9个月前
- 情殇梦断玉阶前
- 曾经的青梅竹马,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这段虐恋情深,令人叹息,空余无尽遗憾。曾经两小无猜的美好,终究被命运碾得粉碎,这段虐恋,徒留一地悲伤,......
- 3.8万字9个月前
- 花惜洲
- 简介正在更新
- 0.7万字8个月前
- 我这么好看,不当海王可惜了!
- 我苏洛卿二十一世纪的五好青年,爱好“男”只要长的帅我都爱,我的梦想是“给所有帅哥一个家”。但是!28岁正是浪的好年纪,就给我来了一个穿越。不......
- 3.8万字3个月前
- 执迷书
- 他与他是是兄弟,从小在隐世宗门无尘殿一起学习。两小无猜情义无价。可是命运安排他们分别五年后,走向了敌对的阵营。他知道他的帝王之路必定困难,应......
- 4.3万字1个月前
- 喜美:折南枝
- 友友们,本书前十几章以剧情为主,但二十四章以后就甜甜的了,二十五章发糖了哦,可看本书别名《喜美:淬毒竹香》喜美同人文2025年8月27日开坑......
- 6.2万字4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