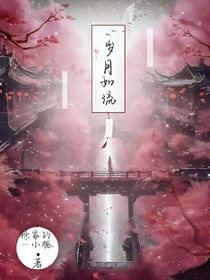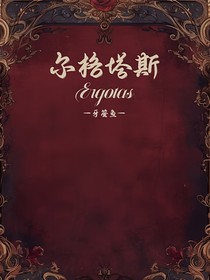第十一章:雏雁绕巢飞 (2-1)
清明时节的苏州,总带着濛濛的雨意。锦雀抱着刚满周岁的雁初,站在忠烈祠的石阶上,看着萧珩将一束白菊放在沈夫人的牌位前。牌位前的铜炉里,新燃的檀香正袅袅升起,混着殿外飘来的杏花香,在空气中漫开淡淡的暖意。
“娘,您看,这是雁初。”锦雀轻轻晃了晃怀里的孩子,小家伙穿着件鹅黄色的小袄,正伸着胖乎乎的小手去够牌位前的供果,“她刚会叫‘外婆’呢,就是发音还含糊,像只小奶猫。”
萧珩将孩子从她怀里接过来,指尖拂过雁初腕间的红绳锦囊——那片锦雀花瓣早已在岁月里褪成浅黄,却被孩子的体温焐得温热。“前几日去楚府旧址,义仓已建成了,”他望着沈夫人的牌位,声音温和如春风,“粮仓的匾额是书铺老者题的,写着‘泽被乡邻’,里面储的新米,够苏州百姓熬过整个饥荒了。”
雨停时,雁初在萧珩怀里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沾着点奶渍。锦雀看着她鬓边新长出的胎发,忽然想起去年洗三礼时,老者说的那句“有福气”,如今看来,这福气不是锦衣玉食,而是能在安稳的岁月里,听着檐角的铜铃,看着孩子慢慢长大。
入夏后,府衙后院的栀子花开得正好。锦雀坐在廊下,看着萧珩教雁初认花。小家伙刚学会走路,摇摇晃晃地扑向花丛,却被花梗绊了一下,跌坐在草地上。萧珩正要起身去扶,她却自己撑着小手站起来,抓起一朵落在地上的栀子花,举着朝锦雀咯咯笑,花瓣上的露水溅在她鼻尖上,像颗晶莹的珍珠。
“大理寺的信上说,京里那位新科状元,竟是当年楚家走私案里获救的书生。”萧珩将雁初抱进怀里,替她擦掉鼻尖的露水,“他在谢恩折里特意提了沈夫人的功绩,说若不是当年夫人留下的账本,他父亲的冤案怕是永远也翻不了。”
锦雀正在缝补的针脚微微一顿。阳光穿过栀子花丛,落在她膝头的布料上,上面绣着小小的雁形图案——这是给雁初做的新肚兜,针脚虽不如苏州绣娘细密,却带着她亲手缝进的暖意。她忽然想起楚府暗河的潮湿、逃亡路上的饥饿、初到苏州时的惶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如今都成了滋养生命的养分,让她更懂得珍惜眼前的安稳。
秋日里,书铺的老者带着个眉清目秀的少年来府衙做客。少年是老者新收的徒弟,据说祖上曾是楚府的账房先生,当年因不愿参与走私,被楚老爷赶出门去,如今靠着抄书度日。
“这孩子写得一手好字,”老者拉着少年的手,指着桌上的卷宗,“说是想跟着萧推官学刑狱文书,将来也能为百姓伸冤。”
锦雀看着少年拘谨却坚定的眼神,忽然想起自己初到书铺时的模样。那时她握着笔的手总在发抖,是老者一句句教她“心正,则笔正”,才让她在案牍间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底气。“后院的书房里有不少旧卷宗,”她笑着对少年说,“若是不嫌弃,可常来翻看。”
少年深深一揖,眼眶微微发红:“多谢顾夫人。家父常说,楚府的罪孽里,总有清白之人的骨头撑着,如今看来,果然如此。”
入冬后的一个雪夜,锦雀被雁初的哭声惊醒。小家伙不知怎的发起热来,小脸烧得通红,小手紧紧抓着锦雀的衣襟不放。萧珩披着棉袄去请医者,锦雀抱着孩子坐在床上,一遍遍地用温水给她擦额头,忽然摸到孩子枕下的银花簪——那是她特意找人仿制的沈夫人簪子,缩小了尺寸给雁初当护身符。
“娘,您要护着雁初。”锦雀低头,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声音带着些微的哽咽,“就像当年护着我那样。”
锦雀归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只有爱你的人才读得懂你
- 准确的来说,男主是个清廉正直的人,而女主女扮男装,吃喝嫖赌,样样都沾,完全和男主根本就是反面教材,这两个人也因此成了死对头,可能是主角光环的......
- 0.4万字5个月前
- 岁月如流……
-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诺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为爱而死,为你而死,遥儿无怨无悔但是愿上天有好生之德愿再无无辜之人惨死,让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让......
- 0.6万字4个月前
- 定情于江湖上
- 在风雨飘摇的王朝中男女主艰难求生,新帝年幼有太后垂帘听政,身上背负着复新的家族使命
- 2.2万字4个月前
- 双璧传
- 时空穿梭:考古学家沈清欢与医学生林知夏在三星堆考古现场意外触发青铜轮盘,引发量子纠缠现象穿越时空。沈清欢魂穿成为镇北侯嫡女,而林知夏则带着现......
- 1.8万字4个月前
- 紫禁:无限回廊
- 为煮啵发电吧!怎么都没有人看。好难过
- 5.7万字2周前
- 尔格塔斯
- 被「罪」侵蚀的世界为本人原创小说,小说内人物均为原创角色
- 2.9万字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