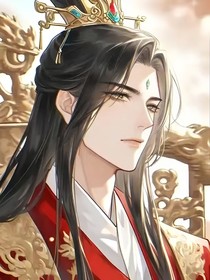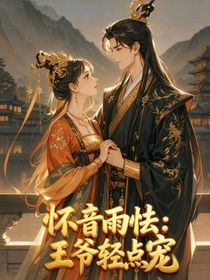第十八章:种痕印山河 (2-1)
夏至的蝉鸣裹着热浪,雁初在西北的学堂后墙,见着片爬满石壁的锦雀花。粉白的花瓣被晒得微微卷曲,花藤却像双有力的手,紧紧扒着石缝里的薄土——正是十年前她摆在窗台上那盆花的后代,如今已把整面墙织成了花帘。
“先生说这花是‘识字的’,”扎羊角辫的女童举着课本跑过来,书页里夹着片压平的花瓣,“您看这页画的义仓,花藤就顺着字爬,像在跟着念‘泽被乡邻’呢。”学堂的屋檐下,挂着串风干的花籽,每颗籽上都用朱砂点了个小点儿,“是去年毕业生留下的,说点了朱砂,种子到了新地方,也忘不了老家的字。”
离学堂不远的驿站里,掌柜的正用锦雀花瓣泡凉茶。粗瓷碗沿结着层细密的水珠,碗底沉着片花瓣,像枚小小的胭脂印。“这花能解暑,”他给雁初斟茶时说,“去年有个岭南来的绣娘,教我们用花瓣染布,说这颜色经晒,就像故事经传。您看这桌布,洗了二十遍,花影还在呢。”
布上的花影确实清晰,是朵锦雀花缠着白雁的模样,针脚里还嵌着几粒细小的花籽。“绣娘说,籽在布上藏着,哪天掉在土里,又是一窝新花。”掌柜的指着墙角的木柜,里面摆着各地的花谱,最旧的那本封面上,贴着片苏州的杏花,旁边写着行小字:“花换花,籽换籽,都是心头事。”
南行的路经戈壁时,驼队的向导从怀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是块干硬的饼,饼上印着朵模糊的锦雀花。“这是波斯来的商队给的,说他们的饼里都掺花籽,”向导咬了口饼,渣子里果然混着几粒黑亮的籽,“他们说花籽在饼里不会坏,就像念想在心里不会凉。”
驼铃叮当声里,雁初发现驼队的水囊上,都绣着朵小小的锦雀花。“是西域的姑娘绣的,”向导摸着水囊上的花说,“她们说这花懂水的性子,跟着走,再远也能找到绿洲。您看这花茎,从囊口绕到囊底,像条走不完的路,却总往有水的地方去。”
回到京城时,庭院里的花架下多了个新竹筐,里面装着各地送来的花器:苏州的青瓷瓶、西北的粗陶碗、波斯的银托盘,每个器皿里都插着支锦雀花,花瓣上还沾着各自的土——青瓷瓶里的花带着江南的湿气,粗陶碗里的沾着西北的沙尘,银托盘里的裹着异域的香料。
“萧珩说,这些花器要编成册,叫《天下花器记》,”锦雀正用软布擦着银托盘,“你看这托盘底的花纹,竟和咱院里花架的纹路差不多,像隔着千山万水认了亲。”她从筐底摸出个布偶,是用各色碎布拼的,身子是岭南的绸,胳膊是西北的麻,脸上贴着片波斯的蓝花瓣,“是孩子们缝的,说这偶身上有各地的花,走到哪儿都有伴。”
萧珩在案前写《善举续录》的新篇,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混着窗外的蝉鸣,像首温柔的曲子。“你带回的戈壁花籽,我种在西墙下了,”他指着墙角冒出的嫩芽,“刚破土就带着股倔劲儿,跟当年你娘在苏州种的第一株一个样。”
案头的砚台里,沉着片锦雀花瓣,墨汁已把花瓣染成了深紫色。“这是用花瓣研的墨,”萧珩蘸了点墨,在纸上写了个“续”字,笔画间竟透出淡淡的花香,“波斯商人说,他们那边用花汁写信,字里藏着花的魂,读信的人能闻见远方的春。”
七夕前,大理寺的年轻官员带着幅画来。画的是片花田,田埂上站着三代人:沈夫人弯腰撒种,锦雀在花架下晒药,雁初牵着个孩子的手,孩子手里捧着颗种子。“这是我家小儿画的,”官员指着画里的银簪,“他说这簪子是根线,把过去和现在缝在了一起。”
雁初摸着鬓边的银簪,簪尾的温润触感里,像藏着无数个春天的温度。她忽然想起驿站掌柜的话:“花走的路,比人长;籽记的事,比书久。”此刻再看庭院里的花藤,新枝缠着老干,老干托着新花,倒真像条缝补时光的线,把散落的岁月,都织成了温暖的模样。
锦雀归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唯愿与君长相守
- 7岁的林允儿被父母丢到浮云山脚下,沈辞安捡到林允儿并收她为徒,多年后,沈辞安渐渐对林允儿感情发生变化,不许她离开身边,林允儿喜欢别人怨恨师父......
- 1.9万字7个月前
- 魂穿古代大小姐之后
- 男主林墨魂穿古代大小姐苏瑶身上被坑爹系统引发的爆笑事件
- 6.0万字3个月前
- 大邹高祖武皇帝
- 大邹王朝
- 41.2万字2个月前
- 废后离宫后,他疯了
- 《废后离宫后,他疯了》-故事视角:第一人称我嫁给他那夜,红盖头未曾掀起。堂堂太子,宁愿守着冷床坐到天亮,也不愿见我一眼——因为他心尖上的白月......
- 6.9万字2个月前
- 怀音雨怯:王爷轻点宠
- 【古风+先婚后爱+双洁HE+甜宠】崔怀音是父母双亡的国公府长女,容貌映丽,性子温软,从小在府里过得小心翼翼,后来皇上赐婚将她指给远在北疆......
- 0.5万字1周前
- 杂粮番外
- 文章都是ai的,然后我想把这个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记得真的写的挺好的,很带感
- 1.0万字22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