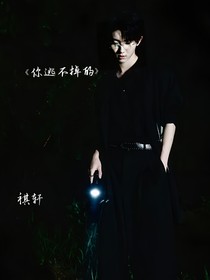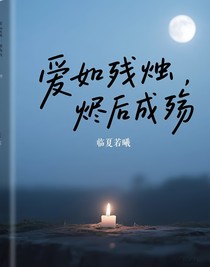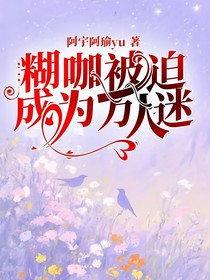雪落与回声 (2-1)
大雪封了回春巷的那天,布庄的烟囱冒起了白烟。苏晚把新染的藏青色丝线绕在线轴上,线轴转得飞快,在雪光里甩出淡淡的蓝影,倒像把天空的颜色缠成了圈。
“念念的寒假作业要做‘声音拼图’,”陈砚正给壁炉添柴,火星子溅在炉边的青砖上,烫出小小的黑痕,“把去年录的布庄声音剪剪拼拼,说要做成首‘家的歌’。”他捡起块掉在地上的木炭,在雪地上画了个简易的乐谱,音符像串歪歪扭扭的糖葫芦。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雪映手艺”装置来了。他们在布庄院子里搭了个透明的玻璃棚,棚顶铺着层薄雪,让手艺人在棚内的白布上创作——苏晚绣雪枝,针脚要轻得像雪落在枝桠;陈砚画雪景,墨色要淡得透出布的肌理,再让棚外的雪光透过白布,把作品映在对面的墙上,像给雪景加了层会动的影子。
“我们想在棚角留块毛玻璃,”年轻人指着棚子的角落,“让外面的人用手指在雪上写字,字的影子会落在白布上,手艺人就能跟着影子创作,算是雪天里的隔空搭伙。”
苏晚取来银灰色的丝线,在白布上绣起松针。针脚密的地方,雪光透过来就成了深影,疏的地方则是浅影,绣到松梢,故意让针脚歪了几处,像被雪压弯的枝桠。“雪本来就不规整,”她穿针时说,“太齐整了,倒不像真的。”
陈砚在白布的空白处画了串脚印,从玻璃棚门口一直延伸到松树下。有的脚印深,是带着工具的沉;有的浅,像孩子追着雪花跑的轻;最末个脚印旁,画了只衔着绣线的麻雀,翅膀上的雪片用留白代替,倒像真的会抖落下来。
“雪会化,但影子能留下,”他给脚印描边时说,“就像老手艺,看着像被雪盖住了,其实根在土里冒热气呢。”
冬至那天,玻璃棚成了“雪天工坊”。修鞋匠带着锥子来,在白布上扎出雪地上的冰裂纹;补旗袍的老太太用银丝绣了片雪花,说要和年轻时绣的嫁衣凑成“冬春对”;连机器人工程师都来了,让机械臂在角落绣了个小小的雪人,雪人手里的扫帚,用的是苏晚早年绣坏的竹枝纹样。
念念举着录音笔在棚里跑,录下针穿过布面的“沙沙”声、木炭划过白布的“簌簌”声,还有棚外行人在雪上写字的“咯吱”声。“这些声音冻在雪里,”她对着录音笔说,“春天化了,就能顺着水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有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在棚外的雪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绣绷,影子落在白布上,苏晚立刻跟着影子绣起来。针脚刚落,女孩又画了只蝴蝶,陈砚便取来墨笔,在蝴蝶翅膀上添了几笔,和苏晚当年绣在空绷上的那只重合。
“这叫雪上传书,”女孩的奶奶笑着说,“比写信快,还带着雪的凉劲儿。”
小寒那天,雪下得更大了。玻璃棚外的雪积了厚厚一层,把棚内的影子映得格外清晰。苏晚发现,松针的影子在墙上轻轻摇晃,像真的被风吹动;陈砚画的脚印影子里,竟落进了片真实的雪花,融在墙上,洇出小小的水痕。
“雪在帮咱们补画呢,”陈砚指着水痕笑,“知道咱们没画够。”
念念把录好的“家的歌”放了出来,里面混着壁炉的柴火声、绣针的穿梭声、还有陈砚画雪时木炭掉在地上的轻响。雪光透过玻璃棚,把声音的影子投在雪地上,像串跳动的音符。
“你听,”她拉着苏晚的手,“雪在跟着歌跳舞呢。”
傍晚收工时,他们在玻璃棚的毛玻璃上,用手指写了行字:“雪落有痕,手艺有声”。雪慢慢盖住字迹,却把影子深深印在了白布上。苏晚取来金线,沿着影子的轮廓绣了遍,针脚重得像要把字钉在时光里。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渐远的爰
- 《渐远的爱》是一部探讨爱情、成长与自我发现的小说。故事围绕着主人公林晓展开,她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恋情后,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希望在那里找到新......
- 1.1万字7个月前
- 祺轩:你逃不掉的
- 强制爱总裁祺X无助轩
- 1.5万字6个月前
- 朱颜旧梦
- 朱颜辞镜花辞树,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恨不知所终,一笑而泯
- 1.3万字6个月前
- 替身文学之我是自己的替身
- 副本故事,副本内容为考试。故事内容为双男主,请慎重选择。不喜勿喷。
- 0.4万字5个月前
- 爱如残烛,烬后成殇
- 叶欣然和林悦涵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人而闹掰。
- 1.5万字2周前
- 糊咖被迫成为万人迷
- 娱乐圈十八线小糊咖苏暖暖,因直播翻车沦为全网笑柄,被经纪公司放弃、深陷退圈危机。就在她以为梦想破碎时,一条神秘短信将她引向城郊废弃工厂,获得......
- 3.1万字4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