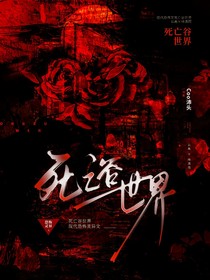霜降与针传 (2-1)
霜降的清晨,回春巷的石板路上结了层薄霜。苏晚推开布庄的门,看见檐下的铜风铃裹着层白,铃舌上的“砚晚居”三个字被霜勾勒得格外清晰,像谁用银线细细描过。她弯腰扫霜时,扫帚尖勾到块硬硬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片绣着半朵梅的布角,布面已经脆得发僵,针脚却还牢牢锁着,是母亲当年最拿手的“盘金绣”。
“这是当年给陈家奶奶做寿衣时剩下的,”陈砚正往砚台里倒温水,指尖触到冰凉的墨锭,忽然想起什么,转身从樟木箱里翻出个红布包,里面是副绣架,架子的木棱上刻着个小小的“砚”字,“那年我出国前,你娘说‘手艺得有人传,就像这架子,得有人扶着才能立住’,非要把这副给我。”
苏晚把布角凑到阳光下,盘金绣的金线在霜光里泛着冷黄,像凝固的阳光。她取来新的金线,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断了的针脚接起来,接痕处故意留了点毛边,像霜落在梅瓣上的绒毛。“老针脚不能全磨平,”她对着光看接缝,“得让学的人知道,当年的手也抖过,才更敢下针。”
进阶班的年轻人带着“针脚图谱”来了。他们把各代手艺人的针法做成了立体模型:苏晚母亲的盘金绣用铜丝模拟金线的硬挺,苏晚的乱针绣用彩色棉线表现丝线的流动,甚至连念念绣坏的兔子耳朵,都用软陶捏了个歪歪扭扭的样品,旁边配着视频讲解:“错针脚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像路上的石子,能让人走得更稳。”
“我们想做个‘传针盒’,”年轻人指着个檀木盒子,“每个学手艺的人领盒时,放根自己的针进去,学会了就换根新针,把旧针留给下一个人,让针脚里的力气代代传。”盒子的内壁刻着圈细密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都标着日期,最早的一格空着,旁边写着“留给第一位手艺人”。
苏晚选了根母亲用过的盘金针,针尖已经有些钝,她用绒布擦了又擦,放进最老的格子里。“这针走过的梅瓣,比巷口的老梅树开的花还多,”她盖盒时说,“该让它歇在这儿,看着新针接着走。”
陈砚在盒子的 lid 上画了串针影,从第一格的盘金针,一直排到最后一格的新针,每个影子的末端都缠着根线,线的颜色从深金到浅彩,像时光慢慢晕开的色。“针是死的,”他给针影描边时说,“但线是活的,缠在一起,就能把力气传下去,就像回春巷的人,看着看着就学会了彼此的样子。”
立冬那天,布庄成了“传针学堂”。苏晚坐在母亲的绣架前,教孩子们盘金绣,手里的针故意慢半拍,让孩子们看清楚每道转弯的力道;陈砚则在旁边画针法示意图,画到念念绣坏的兔子耳朵时,特意把线条画得歪歪扭扭,旁边注着“错得可爱,比对的更让人记牢”。
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总学不会盘金绣的转弯,急得直掉眼泪。苏晚把母亲的盘金针递给她:“你摸摸这针尖,当年我娘绣到半夜,针比这还烫,也照样错。”小姑娘握着旧针,忽然就绣顺了,针脚虽还有点歪,却比刚才多了几分笃定。
“针在教我呢,”她举着绣好的梅瓣说,“它告诉我‘别急,慢慢走’。”
机器人工程师带着机械臂来了,这次的机械臂上装了压力传感器,能模仿人手的轻重——学盘金绣就调大力度,学乱针绣就减小压力,绣出的梅瓣竟有了几分人的温度。“机器能学力度,”他在传针盒旁贴了张纸条,“但学不会‘差不多就行’的温柔,这得人传。”
念念背着自己的传针盒,给新来的孩子发针。她的盒子里已经有三根针:第一根绣坏了兔子,第二根绣好了脚印,第三根正在学盘金绣,针尖还沾着点金线的碎屑。“这根针最聪明,”她举着第三根针说,“它记住了奶奶的针怎么走,正教我呢。”
锦绣记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如果恍如初见
- 我们可以在见一面吗?我想你了
- 0.7万字6个月前
- 死亡谷世界
- 双女主离云×林清雨那晚遭遇的凶险只是离云看清这个世界的开始。选择这条道路原本暗淡无光的世界却度上滤镜,演变成人们口中的童话世界那手上粘上的又......
- 0.8万字6个月前
- 女推2:双生花
- 内容完善中
- 0.7万字5个月前
- 黑色世界邀请函
- 双女主/群像/无限流/原创小说吕熠莹×柳依阁“白色守望者,必胜!”六边形战士:吕熠莹冷静心理学脑力担当:柳依阁腹黑怼人神秘女孩:谢温林占卜魔......
- 5.7万字2周前
- 渣女的第九十九次恋爱
- 姜晚吟因系统设置必须多次与傅渊分手,其执行任务为,只有被男主真心喜欢,并且进行多次分手后,才可以真正结束任务。
- 0.3万字1周前
- 快穿:贱人就是矫情
- 华妃娘娘说过:贱人就是矫情!
- 0.5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