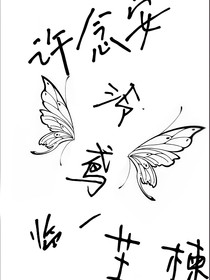岁月在替我们数着
入秋时,戏园新来了批学戏的孩子,其中有个眉眼弯弯的小姑娘,总爱缠着陈砚问沈玉茹的故事。她学唱《梅花笺》时总找不准韵脚,陈砚便取来那支沈玉茹用过的银簪,簪头雕着半开的梅朵,轻轻敲着桌面教她:“这里要像梅瓣落进水里,轻些,再柔些。”
小姑娘学得认真,某天练完戏,突然指着镜台上的胭脂盒笑:“陈爷爷,您看!”盒里那半块胭脂不知何时少了些,缺口处竟晕出淡淡的红,像极了沈玉茹当年演《贵妃醉酒》时,唇角那抹被风吹淡的艳色。更奇的是,镜面上凝着层薄霜,霜花漫过之处,竟显露出几行浅痕,是《梅花笺》里的唱词:“梅香入墨痕犹暖,弦音绕梁梦未寒。”
霜降那天,陈砚在戏台角落翻出个旧木箱,里面是沈玉茹当年攒的戏本,每页空白处都画着小小的梅枝。翻到最后一页,夹着张泛黄的纸条,是他年轻时写的胡琴谱,谱子旁有行娟秀的小字:“砚哥拉琴时,指尖会沾梅香呢。”他摩挲着字迹,窗外的老梅树突然落下片枯叶,正巧落在谱子上“相思”二字中间,像枚被时光磨旧的印章。
大雪封门的夜里,陈砚守着铜炉打盹,梦见自己站在梅树下,沈玉茹穿着那件未绣完的帔衫,正低头绣最后半朵白梅。她指尖的银线在雪光里闪,他想开口,却见她抬头笑:“砚哥你看,这梅蕊要蘸着雪水绣才鲜活。”话音落,帐外的铜炉“噼啪”响了声,他惊醒时,发现炉边的帔衫下摆,那半朵白梅竟真多了丝银线,像刚被谁添了针脚。
开春后,戏园的老梅树开花了,满枝的红萼映着戏台,竟比当年沈玉茹演《梅花笺》时的布景还要艳。学戏的少年们排着队摸那挂在枝头的锦囊,有个孩子突然喊:“里面有东西在动!”陈砚取下锦囊打开,只见去年扫进去的霉花和干梅蕊,竟长出了颗小小的梅籽,裹在层半融的胭脂里,像颗藏在时光里的红豆。
他把梅籽埋在老梅树下,浇水时指尖触到泥土,竟沾了点黏黏的甜,是胭脂混着梅蜜的味道。穿水红衫的小姑娘蹲在旁边数花瓣,突然指着树影笑:“陈爷爷你看,树影在写‘念’字呢!”陈砚抬头,日光穿过枝桠,落在戏台板上的光影果然弯弯曲曲,像他无数个夜里,在胡琴谱上反复写的那个字。
入夏的第一场雨来临时,梅树下冒出了株嫩芽,顶带着点胭脂色的晕。陈砚坐在戏台边拉琴,调子还是那曲《梅花笺》,拉到“岁岁梅开如旧约”时,琴弦突然震颤了下,抬头望去,只见新抽的梅枝上,竟缠着缕极细的红绳,和记忆里沈玉茹腕间的那道一模一样。
雨停后,学戏的少年捧着新画的戏报跑来,上面是他和沈玉茹的画像,背景是满树梅花。“陈爷爷,我们把您的故事画成戏了!”少年笑得灿烂,陈砚接过戏报,发现画像里沈玉茹的戏服下摆,那半朵未绣完的白梅,不知被谁补全了,针脚细密,像无数个日子里,悄悄漫过心头的暖。
他把戏报挂在后台,正对着那盒胭脂。梅雨季的潮气又来,这次胭脂盒里没泛水光,却长出了层薄薄的白霜,霜花聚在刻字处,把“砚哥的胡弦,比胭脂更能勾人魂”映得愈发清晰。窗外的新梅枝在风里晃,锦囊里的梅籽已抽成细苗,红绳缠着枝桠,像句被岁月系住的诺言。
胡弦再响时,陈砚忽然明白,有些约从不是“等”出来的,是梅树记得开花,是琴弦记得旧调,是他每次拂过戏服上的针脚,都能触到的那点暖。就像此刻,新梅枝上的红绳被风一吹,轻轻敲着戏台的栏杆,声音清脆,像沈玉茹当年总爱说的那句:“砚哥,你听,岁月在替我们数着,年年。”
碎镜中的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兄坑:如果前大变魔修了的话
- 轮回一次,前大如果麻木做正道,选择了魔修会怎么样?
- 0.1万字5个月前
- 青铜锁与万历奇旅
- 现代高中,历史迷林羽轩等人,因神秘凤灵与一道金光,穿越至明朝万历年间。此时,神秘组织正觊觎能颠覆历史的青铜锁。在万历,他们遭遇追杀,结识历史......
- 3.6万字4个月前
- 圣枪骑士的好朋友怎么会是吸血鬼?
- 从孤儿院初入社会的弗朗西斯竟然被女吸血鬼贵族看中并被转化为血族!但他最好的朋友杰克却是与吸血鬼有血海深仇的吸血鬼猎人!他们会决裂吗?还是联手......
- 2.4万字4个月前
- 心镜四季
- 画家林深因车祸失去右臂,隐居东北雪乡,在教堂废墟中开启左手绘画的涅槃之旅。偶遇研究王阳明的老教授周守真,通过书信体心学对话与雪夜独白,逐步参......
- 67.2万字2周前
- 暗纹优等生
- 0.6万字1周前
- 国服四人寝
- 无限流无cp
- 0.6万字16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