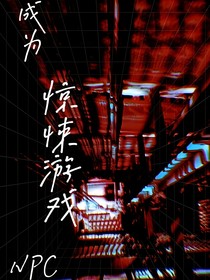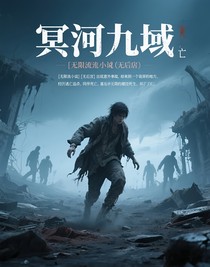岁岁都相见 (2-1)
新梅枝抽条时,陈砚找出那把磨得发亮的胡琴,琴杆上的梅纹被摩挲得温润。他坐在老梅树下调试琴弦,小姑娘抱着戏本凑过来,指着琴轴上缠着的红丝问:“这是沈奶奶留下的吗?”话音刚落,风卷着片新叶掠过琴弦,“嗡”的一声颤音里,竟混着极轻的笑声,像谁在枝头应了句“是呢”。
入秋的戏园格外热闹,孩子们排演的《梅花笺》要登台了。眉眼弯弯的小姑娘扮上了沈玉茹当年的角色,眉心点的胭脂,正是从那半盒旧胭脂里刮的。陈砚帮她别上银簪,簪头的梅朵刚触到鬓角,后台的铜镜突然亮了亮,镜中映出两个重叠的身影——小姑娘的新扮相,和泛黄戏报上沈玉茹的模样,竟连眼角的弧度都分毫不差。
开演前,陈砚在台下拉琴。弦音刚起,戏台两侧的烛火突然齐齐跳了跳,把“梅香入墨痕犹暖”的楹联照得透亮。演到“弦音绕梁梦未寒”时,老梅树的影子被月光投在戏台上,枝桠的晃动正好跟着唱腔起伏,像沈玉茹当年总爱跟着调子轻摇的折扇。
有个穿长衫的老者看完戏,握着陈砚的手红了眼眶:“我小时候看过沈老板的《梅花笺》,她谢幕时,鬓边的梅簪会掉片花瓣,和今天这小姑娘一模一样。”陈砚望向后台,小姑娘正低头捡簪头掉落的琉璃梅瓣,那花瓣滚到胭脂盒旁,竟和盒里晕开的红痕融成了团,像滴未落的胭脂泪。
深秋整理戏箱时,陈砚摸到个硬纸包,拆开是件半旧的水红裙袄,领口绣着极小的“茹”字。他把裙袄铺在阳光下晒,风过时,布料上的褶皱慢慢舒展,露出藏在衣襟里的半片梅瓣——不是今年的新花,是带着陈年香气的干瓣,边缘还沾着点胡琴松香的痕迹。
孩子们在梅树下挖雪窖藏冬酿,铁锹碰到硬物时,挖出个青瓷小罐,罐口封着的棉纸上,用胭脂写着“待梅开”三个字。打开罐子,没有酒气,只有满罐晒干的梅花,层层叠叠压着张胡琴谱,是他失传多年的《梅落笺》残页。陈砚把谱子铺在石桌上,新梅枝的影子正好补全了缺漏的音符,像沈玉茹隔着时光,替他填完了未竟的旋律。
冬至那天,戏园的铜炉烧得正旺。陈砚抱着新抄的《梅落笺》谱子打盹,梦见沈玉茹坐在炉边烤梅饼,火星溅到她袖口,烧出个小小的梅花形破洞。他惊醒时,发现自己袖口不知何时沾了点焦痕,形状竟和梦里的破洞一般无二。窗外的老梅树落了阵花雨,有朵恰好落在谱子上,把“相思”二字盖得严严实实。
开春的第一堂教戏课,陈砚教孩子们唱《梅落笺》的新调。小姑娘唱到“红绳系枝桠”时,突然指着窗外笑:“红绳在点头呢!”众人望去,新梅枝上的红绳正随着风轻轻叩击树干,每叩一下,就有片花瓣落下,在地上拼出断断续续的痕,像谁用花写了封长信。
陈砚把那半片陈年梅瓣夹进新谱子,夹页处突然显出浅淡的字迹,是沈玉茹的笔锋:“砚哥的谱子,该有梅香才好。”他抬头时,看见阳光穿过胡琴的弦,在谱子上投下细细的金线,把每个音符都镀得发亮,像无数个冬夜里,炉火烧暖的那些时光。
梅树又开花时,戏园来了位银匠,说要给孩子们打新的梅花簪。陈砚取出那支旧银簪让他仿样,银匠打磨簪头时,突然“咦”了一声——簪子内侧刻着极小的“共岁”二字,被梅朵的纹路藏了几十年,竟在新磨的光线下露了出来。
新打的梅花簪分给孩子们那天,陈砚把旧簪别回老梅树的枝桠上。风过时,新旧梅簪的影子在地上交叠,像两双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小姑娘指着树影唱新学会的词:“梅花开了又谢,胡弦断了又连,你说的年年,原是岁岁都相见。”
碎镜中的她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激发潜能吧!赛稀奥特曼!
- 自创的新时代女奥特曼!喜欢看奧特曼的女孩有福啦!!!不喜勿喷!!!!感谢支持!!!!没有感情线!!!!
- 1.5万字7个月前
- 小蓝星的故事书
- 讲小蓝星的故事书
- 9.1万字7个月前
- 侦探与作家
- 著名作家当侦探,寻找对象竟然是自己
- 7.4万字7个月前
- 无限流:成为惊悚游戏NPC
- 游篱进到惊悚游戏世界,莫名成了NPC.其他NPC都在吓人,只有游篱在吓鬼。疗养院副本游篱努力扮鬼吓人,反被提着电锯的疯批大佬玩家追得嗷嗷叫。......
- 9.8万字5个月前
- 冥河九域
- 神秘世界,这里没有太阳,天空永远是一片诡异的纯白色,四周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白雾,枯萎的树木扭曲着枝干。来到这里的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来到这里,......
- 3.8万字4天前
- 金铃蝶梦
- 蝉鸣声响起愿我们好在盛夏
- 1.8万字19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