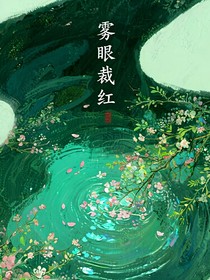第一章 雨叩朱漆,旧音生 (3-1)
小满刚过,江南的雨便开始绵绵不绝,仿佛带着无尽的眷恋,将这片水乡浸润得愈发柔和。雨丝如银针般细密,无声地洒落在青石板的小巷、碧绿的荷塘与远处黛青色的屋檐上,织出一卷氤氲的水墨画。空气里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夹杂着初夏新荷的清香,让人不由得沉醉在这朦胧的诗意中。
细雨如丝,斜斜地飘落,将苏州城的青瓦白墙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宛如一幅渐渐晕染开的水墨画卷。平江路幽深的巷弄尽头,隐匿着一座毫不起眼的宅院。朱漆斑驳的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黑檀木匾,匾上刻着“听雪斋”三个篆字,笔锋清瘦冷峻,犹如雪后枝头孤傲的寒梅。雨滴轻轻落在匾额上,墨迹仿佛随之化开,渗出几分深邃的暗色,仿佛那字里行间藏着未尽的故事,悄然浸润在这无声的雨幕中。
林清宴坐在窗边的梨木桌前,指尖捏着一根银针,正小心翼翼地挑着一把古琴的断弦。琴是唐代的“焦尾”,琴身有一道细微的裂痕,是去年从一个败落的世家收来的。她挑断最后一丝粘连的弦,指尖在琴面上轻轻拂过,琴身忽然发出一声极轻的嗡鸣,像有只蛰伏了千年的虫,在里面舒展了一下翅膀。
“姑娘,这琴……当真还能修?”站在桌旁的老管家福伯捧着个锦盒,盒里装着新做的丝弦,银丝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光,“前儿个那琴师来看了,说这裂痕伤了龙池,就算修好,音色也回不来了。”
林清宴抬眸,眼睫上沾着点雨雾,像落了层细霜。她的眼睛生得特别,瞳仁是极浅的榛子色,在阴雨天里泛着朦胧的光,看人时总带着点漫不经心的专注,仿佛能透过皮囊,看到骨子里去。
“能不能回得来,得听它自己说。”她的声音清润,像雨后青石板上流淌的细流,“你听——”
她指尖在琴尾的凤沼处敲了敲,那里嵌着块小小的绿松石,已经磨得发亮。随着她的敲击,琴身又发出一声嗡鸣,这次的声音更清晰些,带着点委屈似的颤音,像被遗弃的孩童在低泣。
福伯愣住了,侧着耳朵听了半天,只听到窗外的雨声:“姑娘,老奴……啥也没听见啊。”
林清宴笑了笑,眼尾弯起一道浅弧,像新月落在水面。“您听惯了人声,自然听不见它的话。”她从锦盒里取出新弦,银丝在她指间灵活地穿梭,“这琴,以前是位公主的贴身物,安史之乱时,她抱着琴投了护城河,琴没沉,漂到了民间,可琴心里的那点魂,一直记着水里的冷呢。”
福伯啧啧称奇:“公主的琴?那可是宝贝了!”
“是宝贝,也不是宝贝。”林清宴把新弦固定在琴轸上,调了调弦音,“物件的好坏,不在身价,在它记了多少事。”
“听雪斋”是苏州城里最特别的铺子,说是铺子,却从不开门迎客,只在门上挂个木牌,写着“收旧音,修余响”。来的都是老主顾,大多是些收藏古物的世家,或是研究乐理的学者,求的不是林清宴修物件的手艺,而是她那手“听声”的本事——她能从老旧的器物里,听出曾经附着在上面的声音片段。
三年前她从北方来,带着一把断了弦的琵琶,在这平江路深处租下这座宅院。起初没人信一个年轻姑娘有这能耐,直到去年,城西的顾老爷要嫁女儿,陪嫁的一套银餐具总透着股怪味,林清宴来了,只摸了摸那银碗,就说这套餐具二十年前曾用来盛过毒药,毒死了顾老爷的原配夫人,碗底还沾着点苦杏仁的气息。顾老爷起初不信,派人翻查老宅,果然在当年夫人住的院子里,挖出了一具骸骨,脖颈处有明显的勒痕,而那套餐具,正是当年夫人的陪嫁。
打那以后,“听雪斋”的名声就传开了。有人来修传家的古琴,想听听祖辈弹琴时的欢声笑语;有人来问祖传的玉佩,想知道上面是否沾过主人的血泪;甚至有官府的人偷偷来,求她听听一桩旧案里的凶器,希望能找到些蛛丝马迹。
余响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捡了个无cp男主后
- 不想写,审核不过呜呜,都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就一句话:捡了个美人媳妇后。加长版文案:白粟栓捡了一个人,冰清玉洁,肤白貌美。一开始他觉得自己压根......
- 1.1万字7个月前
- 不管重来多少次仇人家的孩子总会爱上我
- 顾云飞发现不管自己如何对待仇人家的孩子,他总会被他爱上,而且总会循环往复的回到他见到仇人家的孩子的一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6.2万字7个月前
- 雪落今朝
- 我的枕边人竟然隐藏身份,想偷血丹,反目成仇,但却又放不下隐藏在心中的情感,就是那一丝丝不忍心,让公子动了心,隐藏在心中的爱,终于忍不住,要破......
- 1.9万字6个月前
- 穿越之攻略反派BE手册
- 穿越进古代小说,攻略反派
- 4.5万字5个月前
- 朝拟人:纸上江山
- [当黑夜被烟花点亮,我们便在璀璨光芒之上,静静注视着那位天之骄子]
- 1.4万字3周前
- 雾眼裁红
- 她是勾栏深院里的蒙面舞者,一双眼藏着寒潭与星火,看客为眸光沉溺时,刀锋已吻上咽喉。他是座上常客,看她千次旋转,终在雨日邀一杯冷茶。雨打窗棂时......
- 1.4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