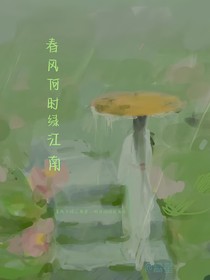第二章 雨夜心事,暗流生 (5-2)
平江路的石板路上,已经没有了行人,只有巡逻的兵丁举着灯笼,脚步匆匆地走过,灯笼的光在湿漉漉的石板上晃出长长的影子。远处的河道里,停泊着几艘乌篷船,船头挂着的马灯像瞌睡人的眼,昏昏沉沉的。
就在这时,她的目光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攫住,骤然停驻。
在听雪斋对面的巷口,有一个模糊的黑影,正躲在槐树后面,偷偷地往这边张望。那黑影穿着蓑衣,戴着斗笠,看不清样貌,但身形佝偻,不像是寻常的路人。
林清宴的心跳微微一滞。
是冲着她来的?还是冲着萧彻来的?
她不动声色地关上窗户,转身走到书架前,假装在找书,眼角的余光却始终留意着窗外的动静。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窗外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像是有人离开了。
她缓步走到门边,微微侧身,透过门缝向外窥探。巷口处,那抹令人不安的黑影已然消失无踪,只余下一串浅淡的脚印,像是某种匆匆离去的痕迹。然而,雨水无情地拍打着地面,不过片刻,那些脚印便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唯剩湿润的青石板泛着冷冽的光泽。
看来,萧彻的到来,已经惊动了某些人。
林清宴的眼神沉了沉。她原本只想在这听雪斋里,安安静静地修她的琴,听她的旧音,把那些不愿想起的往事,都藏在断弦的琵琶里。可萧彻带着那支竹笛出现,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不仅搅乱了她的心绪,也把她重新拉回了那些她试图逃离的过往。
“既然躲不掉……”她低声自语,指尖在窗棂上轻轻敲了敲,发出清脆的声响,“那便查个清楚吧。”
她走到桌前,铺开一张宣纸,研墨提笔。她没有写别的,只是凭着记忆,画出了萧彻带来的那支竹笛的样子,尤其是笛尾那个小小的缺口,和上面刻着的细密云纹。画完之后,她又在旁边写下“北境军”、“虎头令牌”、“归雁谣”几个字,笔尖悬在半空,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添上了“雁门关”三个字。
这三个字像烙铁一样,烫得她指尖发麻。
十年前的雁门关,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吹着《归雁谣》死去的士兵,和她怀里的断弦琵琶,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窗外的雨,还在下着,淅淅沥沥,像是在为那些被遗忘的往事,低声哭泣。
与此同时,北境军驻扎在苏州城外的营地,却是一片肃杀之气。
中军大帐里,灯火通明,映着萧彻冷硬的侧脸。他刚刚审完一个十年前在雁门关服役的老兵,那老兵起初还支支吾吾,说什么都记不清了,直到萧彻将那支竹笛放在他面前,他的脸色才瞬间变得惨白,像见了鬼一样。
“将军……这笛子……”老兵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双手紧紧抓着膝盖,指节泛白。
“认得?”萧彻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目光像淬了冰的刀,直直地盯着老兵,“十年前,在黑风口山谷,你也在,对不对?”
黑风口山谷,就是那个士兵失踪的地方。当年萧彻重伤昏迷,等他醒来时,山谷里只剩下几具蛮族的尸体,还有满地的血迹,那个士兵和他携带的求援信,都不见了踪影。当时的主将说,那士兵是被蛮族掳走了,可萧彻一直觉得事有蹊跷。
老兵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是……属下在……”
“他是怎么死的?”萧彻步步紧逼,“是谁杀了他?那个带虎头令牌的人,是谁?”
老兵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个字。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猛地抬起头,脸上满是恐惧:“将军,别问了!那件事……不能说!说了……我们都得死!”
“死?”萧彻冷笑一声,声音里带着彻骨的寒意,“我萧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就不怕死。但我怕的是,我的弟兄死得不明不白,怕的是军中有内鬼,吃着军饷,却干着通敌叛国的勾当!”
他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油灯被震得晃了晃,灯芯爆出一串火星:“你说!是不是当年的副将赵奎?他手里就有虎头令牌!”
余响记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云是滴墨簪染的雨之仇落情起恩怨了2
- 0.2万字7个月前
- 土土
- 一位冷宫皇子逆袭成为九五至尊后情场失意的故事
- 0.4万字7个月前
- 春风何时绿江南
- 镇国公府欧阳曦与王爷上官禹自初遇便暗动芳心,相互拉扯,终成眷属,但是…
- 2.5万字5个月前
- 考上状元后,满朝威武听我心声
- 沈时序在被封为状元的那一刻,迟到了十八年的金手指终于到了。上辈子他为了救落水的儿童去世,小小年纪就英年早逝,等他再一睁眼就来到了历史上从来没......
- 8.0万字5个月前
- 与君:两生一世
- 前世:木沐(顾言瑾)x周兮宪(周若)蝶杀,一个另人闻风丧胆的阻织。齐国蝶杀少主木沐替身武南候嫡女顾言瑾,收到任务暗杀功高震主的澜沧王,意外知......
- 5.0万字5个月前
- 重生后本宫变渣了
- 【已签约】想当年,本宫可是皇后,后宫独宠,怎么就重生了?重生后本宫居然还变渣了还要行走江湖啊人生不易全靠演技赵轻芸是个好人.绝对的好人
- 7.5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