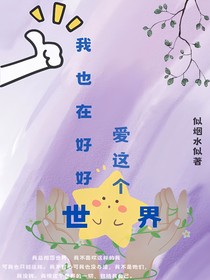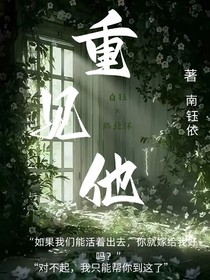第四卷:声痕之上 (2-1)
钟楼的齿轮重新转动的第三个月,城市终于找回了呼吸的节奏。
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落在刚挂牌的“声痕档案馆”门楣上。木质招牌是林野亲手做的,边角还留着不熟练的刻痕,阿镜嫌她手艺糙,夜里偷偷用砂纸磨得光滑些,却被小雅抓个正着——三人围着招牌笑作一团的声音,被林野的录音笔悄悄录了下来,沙沙的电流声里裹着暖意。
档案馆就设在钟楼底层,以前消音局留下的冰冷仪器被挪走,换成了一排排书架和展台。架子上摆着的不是书,而是形形色色的“声痕载体”:老人临终前给孙辈的叮嘱刻在铜片上,新婚夫妇的誓言封在玻璃瓶里,甚至有孩子换牙时掉的乳牙,上面还沾着一句含混的“妈妈我不怕”。
林野坐在前台,指尖划过一个旧怀表——那是爷爷留下的,表盖内侧刻着细小的声纹槽。她按下按钮,怀表便发出轻微的嗡鸣,爷爷修表时的低语从里面渗出来:“小野,记住啊,声音会跑,但心能留住它。”她右眼的义眼已经很久没发烫了,现在她能自由控制它的开关,更多时候,她宁愿用左眼去看那些流动的声痕——它们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晕,像无数条透明的河。
阿镜在里间调试设备。她给档案馆做了套声痕检索系统,指尖在键盘上敲得飞快,屏幕上跳动的声纹图谱里,总混着几帧小雅的声痕——她早上哼的歌、喂流浪猫时的软语、偶尔被他气到时的轻哼。小雅就坐在他旁边的地毯上,给新收集的植物声痕分类,时不时抬头看他一眼,见他屏幕上的“小动作”,便抓起一片银杏叶轻轻砸过去,却被他反手接住,指尖不经意蹭过她的手背,两人都像触电般缩回手,耳尖却悄悄红了。
陆沉成了钟楼的守钟人。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清晨校准钟摆,午后擦拭声纹石,傍晚坐在顶楼的露台上,听档案馆里飘上来的声音。他怀里总揣着半块声纹石,那是女儿留下的,按下开关,就能听见小女孩清脆的笑声:“爸爸,你看我抓到一只蝴蝶!”他会对着空气说“看到了”,声音里带着化不开的温柔,也藏着淡淡的歉疚。有人问他会不会觉得闷,他总是摇摇头:“这里的声音,比任何地方都让人安心。”
消音局解散后,那些曾经被压迫的共鸣者和哑者,渐渐敢来档案馆了。有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每周三都会来,捧着一个褪色的布包,里面是她丈夫的录音带——他是个火车司机,去世前录下了最后一次鸣笛。老太太每次听完,都会抹着眼泪笑:“你听你听,他鸣笛的时候,总爱多按一秒,怕吓着路边的孩子。”
小雅蹲在她身边,轻轻握住她的手。老太太的手很粗糙,却很暖。“奶奶,我帮您把这声音刻在木头上吧,能存更久。”她说着,指了指阿镜刚做好的木盒,“阿镜做的,防潮。”阿镜从里间探出头,正好对上小雅的目光,嘴角弯了弯,又赶紧缩回去假装忙碌,耳根却红得厉害。
林野看着这一切,忽然想起陆沉说过的话。那天陆沉在顶楼给她看女儿的画,画上是个发光的钟楼,底下有好多小人,每个人头顶都飘着不同的音符。“以前我总以为,人是声音的容器,装满了就会炸。”陆沉的声音很轻,“现在才懂,人是回音壁,能让好的声音,一圈圈传下去。”
尾声
五年后的一个傍晚,档案馆快关门了。
林野坐在窗边,摘下了右眼的义眼。玻璃镜片在夕阳下折射出细碎的光,她把它放进丝绒盒子里——现在她已经很少需要它了,那些曾让她痛苦的声痕,如今都能坦然接纳。
录音笔放在手边,她随手按下播放键。
声痕之上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我也在好好爱这个世界
- 我也在好好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能不能也多爱我一点。我要的不多,父母健康长寿,兄弟姐妹健康平安孝顺。如果可以,请给我一点点私心,我想要一个独属......
- 1.1万字7个月前
- 双男文微
- 简介正在更新
- 2.0万字7个月前
- 好消息:穿成男主白月光,坏消息:男主黑化了
- 一觉睡醒,李瑶瑶感觉自己的天都要塌了,哦豁,穿成漫画里男主的白月光。
- 7.5万字7个月前
- 那咋了,你别管
- 由真实事件改编
- 2.4万字6个月前
- 阶上绿痕
- (已签约)一切悲剧的开始,是你想要有一个结果
- 8.0万字5个月前
- 重见他
- 我被路凌接回家后,和路北怀认识,,他表面高冷,不好惹,但是她对我非常好,23岁那年我去SIP到当卧底,最后因为SIP太猖狂,兵部不得不参与,......
- 0.4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