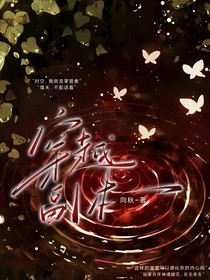墨痕书店异闻录 (4-2)
“孟丫头常来查资料,”周墨生给林夏倒茶,指关节上沾着洗不掉的墨渍,“她祖父是民国时的报人,据说藏了些抗战时期的手稿。这孩子总说要找到那些稿子,证明她祖父不是汉奸。”
林夏的指尖划过茶几上的水渍,那形状像片残缺的银杏叶。“周三下午,她进地窖前跟您说过什么吗?”她注意到书架上有个空位,尺寸正好能放下十六开的线装书,空位边缘还沾着点暗红色的粉末。
“她说找到了《申报》上的记载,”周墨生的喉结动了动,紫砂壶的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日军轰炸城南时,有个报馆编辑带着一批手稿躲进了防空洞,之后就再也没出来。那防空洞的位置,就在现在书店的地窖下面。”
林夏起身告辞时,瞥见书架底层有本翻开的相册。泛黄的照片里,穿长衫的男人站在报馆门口,胸前别着支钢笔,笑容里带着局促。照片右下角的日期被墨点盖住了,隐约能看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字样。她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墨香,不是书纸的味道,而是新鲜的、带着腥气的墨汁味。
四、手稿
陈砚在显微镜下观察那片未燃尽的书页,纤维间残留着奇怪的晶体。技术科的报告刚发过来,这些晶体除了有孟晓雨的血迹,还混合着十九世纪欧洲的铁胆墨水成分——这种墨水含有单宁酸,遇血会变成深蓝色。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林夏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旧报纸扫描件,“《申报》确实记载了那次轰炸,城南防空洞坍塌,死亡人数不明。但档案里没有任何关于报馆编辑的记录,就像这个人从未存在过。”
陈砚突然想起周墨生书房里的相册。那个穿长衫的男人胸前的钢笔,笔帽上有个特殊的纹路,与他今早修复的《考城隍》扉页上的藏书印一模一样。“周墨生的祖父是谁?”他放大照片,发现男人袖口露出半截怀表链,链坠的形状像枚微型印章。
林夏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户籍系统的页面跳出来又被关掉。“查不到,”她皱起眉,“周墨生的户籍资料是十年前补办的,之前的记录全是空的。而且他的年龄登记是五十八岁,但看外貌最多四十岁。”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雨点敲打着书店的玻璃窗,像有人在用指甲抓挠。陈砚走到地窖门口,发现那扇木门不知何时又被关上了,门闩上的头发比早上更长了,在风中轻轻摆动,像水草一样。
五、替身
高中生李默把书包往柜台上一放,搪瓷杯在玻璃台面上磕出声响。他的校服领口沾着墨渍,左手指关节处有道新鲜的划伤,血珠正顺着指尖滴在《楚辞》的封面上。
“周老板,今天有新到的禁书吗?”李默的声音带着变声期的沙哑,眼睛却亮得惊人,“就像孟晓雨借的那种,能看到过去的。”
周墨生的手指在算盘上停顿了一下,镜片后的目光落在李默的伤口上。“那种书阴气重,”他从柜台下抽出个牛皮纸包,里面露出半本线装书,“你确定要看?看了就要遵守规矩,看完必须放回原处,不能带走任何东西。”
李默的喉结动了动。他上周偷看到孟晓雨从地窖出来,手里拿着本发光的书,书页上的字迹像活过来一样在纸上爬行。孟晓雨告诉他,那本书能看到祖父的真实死因,只要用自己的血当墨,就能让书中的人开口说话。
“我确定。”李默接过书,封面冰凉的触感像块墓碑。书名叫《城南旧事》,没有作者,没有出版信息,扉页上用朱砂画着个奇怪的符号,与孟晓雨笔记本上的图案一模一样。
地窖的木门吱呀一声开了道缝,里面飘出淡淡的墨香,夹杂着泥土的腥气。李默握紧书,走进黑暗时,没注意到周墨生正站在柜台后,用沾着墨汁的手指在登记簿上写下他的名字,名字后面画着个倒过来的眼睛。
六、防空洞
林夏的手电筒光束在防空洞的积水中折射出破碎的光斑。这里比想象中更深,洞壁上还留着当年的弹痕,钢筋从混凝土里刺出来,像白骨的断茬。
恐怖异闻:惊悚小故事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龙珠之仙级赛亚人
- 『多平台发布』当一辆失控的异世界传送公交车快速奔腾撞向一名少年,此时天上乌云密布的天空刚好雷劈下来,不知哪里发出来的一把飞刀割喉,经历车撞,......
- 17.9万字7个月前
- 末世诡校
- 男主沉泽本是一所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可就在一天早上,天色灰暗,尘沙飞扬,处处透漏着诡异的气氛,就在第一节上课时,教室灯突然灭了,英语老师张钟暴......
- 1.8万字6个月前
- 穿越副本向秋
- 穿越副本
- 0.2万字6个月前
- 象:水的秘密
- 这是一个星际宇宙空间,也可以称它为平行世界,在这里所有的星座都被分为象。巨蟹,天蝎,双鱼,白羊,狮子,射手,金牛,处女,摩羯,双子天秤,水瓶......
- 0.2万字6个月前
- 九门之厨神
- 怒刷四个诡异世界,省吃俭用,终于存够30万积分,兑换心仪已久的老九门旅游。什么脚踩张启山,怒压老九门,什么成为老九门白月光,陈皮的好朋友……......
- 2.9万字3周前
- 神威漂泊者
- 纵使带土漂泊于世界守护着和平但到底他还是那个在樱花树下没有勇气向喜欢的女孩表白的小男孩琳...哦比托不管前进的道路有多艰难我只希望你能平安归......
- 0.7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