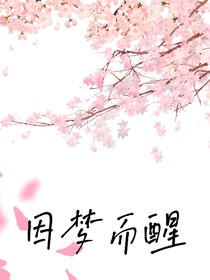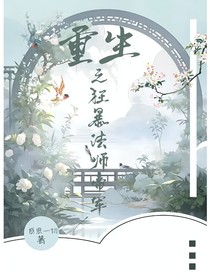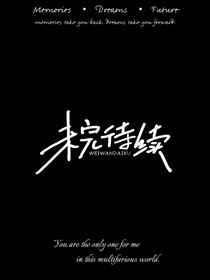黄铜子铳 (2-1)
试爆火药的第二天,草棚里多了三个“新成员”。
是三个流民,两男一女,昨天夜里躲在附近,听见爆炸声,早上就找来了。
“我们……我们想跟着您干,” 领头的男人叫王二,胳膊上有块烫伤的疤,“哪怕给口饭吃,干啥都行。”
周铁山没立刻答应,看向赵夜。
赵夜正摸着那把老铁锉,听着三人的呼吸——都很轻,带着紧张,不像坏人。他问:“你们会啥?”
王二说:“我以前在铜匠铺打杂,会打铜坯。”
另一个男人叫李根,低着头说:“我有力气,能抡锤。”
女人叫春丫,声音细弱:“我……我会搓麻绳,还会看火色(判断温度)。”
赵夜心里一动。打子铳,正缺会弄铜的、有力气的、懂火候的。
“留下可以,” 他说,声音依旧沙哑,“但得听指挥——造出来的东西,不能随便拿,换了粮,按劳分。”
三人连忙点头,王二甚至磕了个头:“只要有饭吃,啥都听您的!”
周铁山看着赵夜,眼神里有点惊讶——这瞎子选人,倒挺准。
但眼下最大的问题不是缺人,是缺料。
“子铳得用铜,” 周铁山摸着那几块硫磺石,眉头皱着,“铁的容易锈,还漏气。可这方圆百里,哪有铜?”
王二忽然说:“我知道!前几天在破庙里,见着个铜香炉,被人砸了,剩个底座,有巴掌大!”
“走!” 周铁山立刻站起来,抓起那把老铁锉。
赵夜也想跟着去,被周铁山按住:“你在这儿等着,我们去去就回。春丫,你留下,跟赵先生说说火色的讲究。”
春丫应了声,蹲在赵夜旁边,捡起一根柴火,在地上画:“火色分三等,发白是太热,发红是正好,发暗是太凉……打铜坯,就得看发红的火候。”
赵夜没说话,伸手摸她画的痕迹,心里记着——他看不见火色,但春丫能看,这就够了。
没过一个时辰,周铁山他们回来了,王二怀里抱着个铜香炉底座,绿锈斑斑,边缘还缺了个角。
“就这,” 王二喘着气,把铜底座放在地上,“够吗?”
周铁山掂了掂,沉得很:“够打两个子铳了!”
李根则扛回一捆干柴,春丫赶紧去垒灶台——今天要化铜,得用大火。
化铜的罐子是周铁山找的,是个破铜盆,底没漏,能架在火上烧。王二负责清理铜底座上的锈,用石头磨,磨出里面的黄亮。
“这是好铜,” 王二摸着磨亮的地方,“庙里的香炉,都是真铜。”
赵夜蹲在灶台边,听着柴火“噼啪”响,闻着铜锈被火烧后的味道,心里盘算着子铳的尺寸。
“子铳长三寸,直径一寸,” 他对周铁山说,“底部留个小凸环,能卡住母铳。”
周铁山点头,捡起根细柴,在地上画了个筒状:“口部要稍薄,方便塞弹丸;尾部要厚,防炸膛。”
春丫蹲在灶台前,盯着铜盆,忽然说:“火够了!铜开始化了!”
众人都凑过去看,铜盆里的铜底座慢慢变软,边缘开始融化,像块黄油,泛着红光。
“加草木灰!” 周铁山喊。
王二赶紧抓了把草木灰撒进去,铜水表面立刻浮起一层灰渣——这是去杂质的法子,军匠的老规矩。
又烧了一炷香的功夫,铜底座彻底化成了水,红得发亮。
“倒!” 周铁山指挥李根。
李根抱起一个用泥做的模子(赵夜昨夜凭着记忆,让他和的泥,捏出子铳的形状),春丫小心地把铜水倒进模子里。
“滋——” 铜水遇冷,发出声响,冒起白烟。
众人都屏住了呼吸,连柴火的“噼啪”声都好像停了。
等铜水凉透,李根小心翼翼地敲碎泥模,里面露出个黄亮的东西——形状歪歪扭扭,像个粗短的铜管,但确实是个“子铳”的坯子。
“成了!” 王二欢呼起来。
盲龙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因梦而醒
- 原本今安是个雪狐妖,在桃花山上生活,在第一次下山的途中,在拍卖场拍下了一个狼妖,今安当时一眼就看出了这个狼妖资质很好,所以才拍下来让他当徒弟......
- 4.3万字7个月前
- 重生之狂暴法师帝君
- 东华帝君重生到2005年奇迹游戏开服前两天。他提前进入游戏,获取唯一的狂暴法师职业,在游戏中,他宛如战神,领先其他玩家的等级和战力。新手村野......
- 10.8万字5个月前
- 宫锁燕无双
- 架空,但以五阿哥为原型,宅斗,宫斗都有,非双洁,不喜误入。
- 2.6万字5个月前
- 重生后公主殿下杀疯了
- 双女主+双男主燕国公主燕梧林重生了,重活一世,什么礼法,什么规矩,通通不要了。她要保护家人,她要让女子入朝为官,她要站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不知......
- 1.8万字5个月前
- 折刀宴
- 0.9万字3周前
- 花好月又圆:毒后归来
- 林晚卿毒发濒死之际,发现重生在祠堂及笄礼上,前世记忆与今生现实产生剧烈冲击-听到母亲提及赐婚三皇子之事,触发复仇决心,情绪失控打碎祭品引发家......
- 13.0万字2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