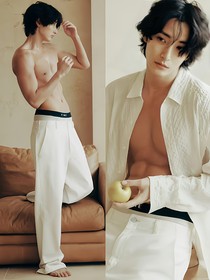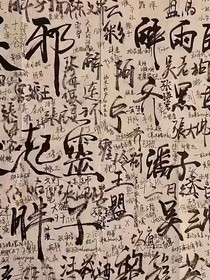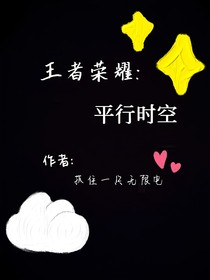柴门初动有归轮 (3-1)
乌檐六驾马车缓过正阳门,午后的日影在车顶鎏金徽记上碎成流动的金星。车帷是礼部特用的玄绡,暗织云鹤纹,风一动,鹤翼掀起一角,露出车内青玉小炉里袅袅沉檀。
驾辕四马一色枣骝,颈系朱缨,蹄声踏在青石御道上,轻重恰好如钟磬三声一顿——这是宋府老管事一早调教好的“入府步”。车辕前端悬着一盏鎏银风灯,灯罩上錾着尚书家的篆体“宋”字,日光下竟像一枚冷玉印章,将整条街的喧嚣都钤住。
转过槐树夹道的牌坊,朱漆大门便豁然洞开。门楼歇山顶,斗拱层层托起“敕建礼部尚书第”六字金匾,匾下十二盏绛纱灯尚未点燃,已先透出森肃。
马车止在丹墀前,车夫勒缰,四马齐垂首,缨穗拂地,似向府内仪门行礼。门内早有两列青衣家仆雁序而出,鸦雀无声,只听得见玉阶下铜鹤香炉里火炭爆出一声轻响。
早早便守候在此的奴仆们,赶忙趋步上前,口中皆是珠玉般的吉祥话语,恭恭敬敬地迎候着老爷夫人荣归府邸。
原来是时任礼部尚书的宋大人回来了。
宋大人原本在青州做刺史,后来京官考核,回京述职,从地方回到京都,“足履实地,不务空名”的为官作风得到圣上赞誉,于是在京都做了礼部尚书。自然,一家老小也都回来了。
早早便守候在此的奴仆们,赶忙趋步上前,口中皆是珠玉般的吉祥话语,恭恭敬敬地迎候着老爷夫人荣归府邸。
帘角微动,一只素手伸出——指尖并不蔻丹,却带着书卷气的淡粉,稳稳扶住老嬷嬷递来的青玉小臂。车帷垂落,玄绡掩住内里的月白裙裾,只露出一角暗绣的芙蓉纹,像一瓣雪悄悄落在宋府的影子里。
穿过两重垂花门,来到家中宋家小姐宋铮铮的闺房。门额上“漱玉”二字是宋大人手书,笔力遒劲,却被珠帘常年筛下的日影磨得柔和。
推门,先闻香——不是浓烈的沉水,是初夏新荷蒸出的冷香,混着一点白檀尾韵,像雨后石阶上最后一丝潮气。窗棂用细绢糊成半透,外头一株西府海棠的影子投进来,随着风,在绣榻上开出暗红的花。
榻是紫檀嵌百宝,却铺着最素净的月白锦褥,只在四角压了极细的银线云纹。榻旁小几,摆着汝窑天青茶盏,盏底卧一尾小鱼,仿佛随时会游进茶汤。
妆台不大,却极其精致:铜镜背面錾着凤穿牡丹,镜面却擦得雪亮,照得人不敢大声。台上并排放着三只小盒——螺钿的盛胭脂,象牙的盛香粉,犀角的盛黛螺。
北窗下是书案,案头一盆建兰,叶尖垂着晶莹的水珠。案上摊开的不是女诫,而是《山海经》和一本《西域记》,书页微微卷起,像是有人刚刚在梦里跋涉过千山万水。
芜花:这地方真大,比青州大多了。只是听不到门外货郎的叫卖声,还有点不习惯了。
青黛:是听不到声音不习惯,还是吃不到青梅果子不习惯呀。
宋铮铮:青黛姐姐,自然是两者都不习惯。这里真安静呀,听不到鸟雀,也听不到阿七们的读书声了。
阿七们是谁?自然是青州云山书院的那群半大小子。不知怎么,回家探亲了之后,书院的好多孩子的声音都变成了鸭子音。晨读时,一群那样的声音格外扰人。
宋铮铮之前是由青黛望风,帮助她出门。后来,一听到阿七们的声音,就知道祖父已经开始授课,自己可以偷偷溜出门了。
五鼓方过,她已散开发髻,用一方青布裹起头发,着窄袖青衫、软底皮靴,腰间悬一柄尺二小纸刀(用来裁书页,也用来削野梨)。
出门时,守门的老仆还打着瞌睡,她或者说是他带着芜花,穿过柳树行,早市已开。她熟门熟路地帮卖酪的老媪写招贴,换一碗热羊乳;蹲在地上与铁匠讨论《考工记》里“金六分其锡而一”的配比,顺手把铁匠打的柳叶小刀别进靴筒。
午后,她沿樵径登云门山。山半有残唐碑,碑阴生满青苔。她以清水泼湿,拓下一角,卷成筒塞进袖中——晚上带回书院,与祖父辩“隶变八分”源流。
衔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玄幻奥特世界
- 唐轩宇,萧焱,罗空,石明四个青年男孩儿都是传说中的四位奥特战士,他们先后在地球防卫军共同组合成一个团队,保卫地球与邪恶外星入侵者抗争的故事。
- 18.9万字7个月前
- 李洙赫——耀眼的你
- 李抚荷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遇到了李洙赫之后,她就沦陷了。
- 28.5万字6个月前
- 盗墓,穿越后我是汪家人!
- 简介正在更新
- 0.5万字6个月前
- 王者荣耀:平行时空
- 王者荣耀各种短篇CP同人文合集!(作者有钱了再整封面)有一定概率加更!
- 4.1万字5个月前
- 王者荣耀:瑶瑶公主在线快穿
- 白糖死了,死得就和她的名字一样,很草率。她幸运地遇到了系统,成为了王者荣耀的瑶,只要完成系统交代的任务,她就可以一直活下去。可是没人告诉她,......
- 0.9万字5个月前
- 推TF四代
- 推文
- 0.3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