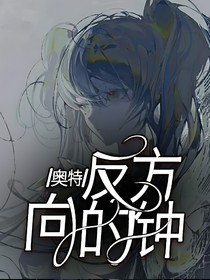深院莺啼春不知 (3-1)
上京的规矩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把宋铮铮圈成了一枚小小的笼中雀。
晨起要先等嬷嬷给她梳头,髻子梳高了,说“端庄”;髻子梳低了,又说“老气”。
午后想去园子里爬那棵老槐树,脚还没蹬上去,就被丫鬟“扑通”一声跪抱住:“小姐,京里不比青州,叫外人看见要笑话的。”
连夜里想溜去街口听一出傀儡戏,也被守夜婆子拿灯笼堵了回来:“上京不比从前,外男杂多,小姐金贵。”
于是日子缩成四四方方一座小院——
上午对着绣绷戳手指,下午对着琴案打瞌睡。
吃食倒精致:金丝酥、玫瑰酪、玉露团……可再甜也填不满心里那只空空的口袋。
她开始数屋檐下的风铃,一天能响三百七十四下;
数墙外走过的轿子,青顶的、朱顶的、蓝呢的,像会移动的盒子;
甚至把《千字文》倒背如流,背到“渠荷的历”时,才发现自己嘴里嚼的是一片枯叶。
最无聊的时候,她就搬梯子去库房,把《青州溪山雪霁图》抱出来。
画轴一展开,雪意扑面而来,她伸手去摸,却只摸到冰凉的绢。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
青州还在,她却不在青州;
画还在,她却把那个敢赌一幅画、敢爬树、敢半夜溜出去啃烤红薯的小姑娘弄丢了。
晚上,她偷偷扯掉两根髻上的金钗,散着发,在院墙根学猫叫。
墙外真有人回了一声“喵”。
她吓得跌坐在地,又忍不住笑,笑得眼泪都出来。
原来想逃出去的不止她一个,
原来墙外也有人,愿意陪她做一只不守规矩的猫。
京城三月,柳色新新,花影重重。
宋铮铮随母亲赴宴,绣鞋刚踏进朱漆门槛,背脊便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提起——颈直、肩平、步缓、笑不露齿。
她规规矩矩行万福,规规矩矩落座,连面前那盏杏仁酪都只舀了七分,留三分在盏里,像给“端庄”二字让位。
可一旦母亲被诰命夫人们缠住,那根线就倏地松了。
她借“更衣”之名溜到后花园。
假山后,小丫鬟正急得团团转——新制的灯芯裙被蔷薇勾破尺余长的丝。
铮铮蹲下身,拔下自己鬓边的鎏银并蒂莲掩鬓,三绕两勾,把裂口挽成一朵活灵活现的缠枝小花。
小丫鬟要跪谢,她一把拽起:“别跪,跪了就真成规矩了。”
回席时,众人正在飞花行令。
轮到一位老大人之孙,七岁小公子背不出诗,涨得满脸通红。
铮铮佯装失手,“叮”地碰落银箸,俯身去拾,顺势在小公子案角写下一个“春”字,又眨眨眼。
小公子福至心灵,脆生生续出:“春眠不觉晓!”
满座皆赞神童,她抿嘴一笑,退回母亲身后,鬓发不乱,耳珰不晃,好像从未离席。
夜散,马车辘辘。
她掀帘一角,看灯火如潮往后退去。
母亲说:“今日你倒乖。”
她垂眸抚过袖口——那里藏着半朵没送出去的缠枝花,和一小片被灯芯裙勾下的嫩叶。
她答:“该守的规矩守了,该帮的人也帮了。”
声音轻得像在对自己说:
“青州没走远,只是学会了在绣鞋底下藏一点泥。”
宋铮铮第一次见到霍长缨,是在一次上京的春猎中。
那日,阳光正好,草色青青,宋铮铮正坐在马车上,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热闹景象。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一匹骏马如风般掠过,马上的人一身劲装,红衣如火,腰间佩剑,英姿飒爽。她定睛一看,只见那女子挽弓如满月,一箭射出,正中远处树梢上悬挂的猎物。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而那女子却只是微微一笑,转身离去,连看都不看众人一眼。
“那是谁?”宋铮铮忍不住问身边的丫鬟。
衔玉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爱丽丝学园之清冷的月光
- 这是一个带着系统的女主穿越到动漫《爱丽丝学园》的故事。作者建议可以去看看动漫《爱丽丝学园》,超好看。作者写这本小说,只是想给这个故事一个完美......
- 3.2万字7个月前
- 凹凸世界看大屏幕:他们
- 凹凸众人看bug,就是大屏幕梗,详细说明看第一章【无cp向(时不时来点糖),情头主要是作者懒得一个个找】【请主动避雷,非常感谢】【不喜勿喷】......
- 4.0万字7个月前
- 萌学园:情深不知深处
- 斯坦小公主诺予卿萌骑士十之星欧趴夸克族史上唯一一位三属性拥有者疗愈系、超能力系以及自然系但也对其身体有所损耗原来我的命定中人是你怪我这么久才......
- 12.5万字6个月前
- 奥特:反方向的钟
- 有私设!!【原创女主】每个选择将成就不同的自己,没有对错只有想与不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可避免,或许有的道路是注定的不妨试一试,失败是必然,......
- 18.3万字6个月前
- 凹凸世界:手握凹凸手游的我天下无敌
- 会员加更两章,鲜花200加更,金币50加更(改一下简介,之前写的老尬)(去给我看作者说)(去给我加群,在作者说,QQ)开学在望,没写作业的林......
- 15.8万字5个月前
- 我的人间烟火:宋焰许沁婚后生活
- 写的是宋焰许沁的婚后生活,后面会有绿茶出现,当然,这只是后话,敬请期待吧
- 0.6万字5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