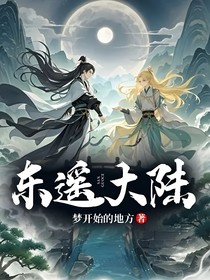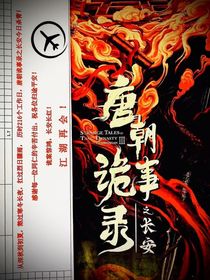十二章 (2-1)
二皇子伏法的消息传到江南时,苏州的荷花开得正盛。粉白的花瓣顶着烈日,把水面铺得满满当当,连晚香楼的栏杆上都沾着淡淡的荷香,甜得有些发腻。
我站在露台上,看青禾用细布蘸着清水,一遍遍擦拭沈家祠堂的牌位。父亲的灵位终于从城西那间漏雨的偏殿挪回了正厅,曾经被污损的“沈讳”二字,被青禾用金粉细细描过,在烛火下泛着冷硬的光。牌位旁新添了个小香炉,燃的是萧彻送的安息香,烟线笔直地往上飘,到房梁处才散,像根扯不断的线。
“姑娘,都察院的文书到了。”青禾捧着卷明黄的绫纸进来,指尖在边缘捏出了红痕,“皇上……皇上给沈尚书平反了,还追了‘忠烈’的谥号。”
我接过文书,绫面冰凉,新印的朱砂在阳光下泛着刺目的红。上面写着“沈家世代忠良,特赦家产归还”,写着“二皇子谋逆伏诛,李御史抄家流放三千里”,写着“凡受牵连者,一律昭雪”。字字句句,都是父亲当年在朝堂上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却冻毙于雁门关风雪中也没等来的公道。
可我摸着那纸,只觉得掌心发僵。父亲死时,怀里揣着未写完的辩书,墨迹被冻成了冰;萧彻沉在暗河时,玄色披风被礁石勾破,露出里面我绣给他的平安符——那符被水泡得发胀,针脚全散了。这迟来的公道,就像江南梅雨季的雨,缠缠绵绵下了满街,却浇不熄漠北冻土下的余烬。
“萧将军呢?”青禾收拾香炉时,忽然抬头问,“他回京城复命,怎么还没消息?”
我望向楼下的码头。三天前萧彻离开时,就站在那片荷塘边。晨光把他的影子投在水里,和荷叶缠在一起。他说北狄残部未清,他得回漠北坐镇,等边境安稳了,就卸甲来江南,陪我看整个夏天的荷花。
我当时没应,只给他塞了包新晒的莲子。他接过时,手指擦过我的掌心,带着漠北的粗粝,像他常年握剑的茧。
佛堂那日的混乱还在眼前。他说二皇子的信是伪造的,说暗河支流的北狄人是来灭口的,说备份的证据是父亲早就让他藏在漠北密窖的。赵副将带来的亲兵也作证,说在暗河下游的冰窟里找到了他,当时他胸口插着半截箭,手里还攥着那卷羊皮纸。
可我没说,我在他衣襟里摸到过一枚狼牙符。银质的,边角被摩挲得发亮,背面刻着北狄的图腾——那是贵族子弟的私物,绝非“缴获”那么简单。就像父亲留给我的密信里,那句被虫蛀了一半的话:“萧彻……北狄……慎防……”
有些事,说破了,连最后一点念想都没了。
“去备船。”我把文书折成小块,塞进父亲牌位底座的暗格里,那里还藏着半块荷纹佩,“去雁门关。”
青禾手里的烛台晃了晃,蜡油滴在地上,凝成小小的珠:“姑娘,沈尚书的衣冠冢已经迁回江南了,雁门关那边……”
“我去看看那棵老槐树。”我打断她,目光落在荷塘深处。有片荷叶卷着边,大概是昨夜被风雨打坏了,“萧彻说过,漠北的雪化了,暗河会涨水,说不定能把沉在底下的东西冲上来。”
其实我知道,冲不上来的。暗河的礁石比刀还利,能把玄铁护心镜撞出裂纹,自然能把人的骨头磨成渣。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消失的地方,风是不是也像江南这样,带着水的潮气。
出发前夜,萧彻的信使来了。骑的是匹快马,马蹄踏碎了苏州的夜。信笺是北狄特有的桑皮纸,粗糙的纸面蹭得指尖发痒,上面只有八个字:“等我回来,共赏荷。”字迹还是那么凌厉,捺脚处带着他惯有的勾,可我认得,那墨是漠北的松烟,带着风沙的涩味。
我把信烧在了香炉里。灰烬飘起来,被青禾打翻的茶泼湿,粘在案上,像一点烧不透的烬。
江南雪,长安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东遥大陆
- 往昔挚友,怀抱壮志未酬,苍天弄人,偶入幽邃结界,两人穿越异界,神祗之恩赐予身,舍却旧我,投身玄门高府。在这异世之旅,共逐男儿鸿志,潜心问道,......
- 36.0万字7个月前
- 梦万疆
- 讲述了现代女主纪疏雨意外穿越到古代,成为将军府庶女的故事…
- 1.3万字6个月前
- 重生后助力丞相登上皇位
- 原名柳红叶,因不小心发现了当今陛下的背后手段,被下毒,她强撑着身子跑到悬崖,因追兵追太紧,你只得纵身一跃.....世传白绫郡主坠崖而亡~〔?......
- 0.8万字6个月前
- 唐朝诡事录:爱与真相
- 玛丽苏小说无脑看自定义
- 11.6万字2周前
- 和亲公主重生后,反手覆江山
- 楚宁潇,楚国五公主,自幼不受亲父待见,倍受凌辱。十六岁那年,为保母亲、幼弟平安,自愿入燕和亲,被封为容妃,倍受恩宠。天真的她自以为遇到了可托......
- 1.6万字1周前
- 双医
- 他是悬壶济世的“墨郎中”,切药像劈柴,寒毒缠身,却为守护一张面具甘愿赴死。他是神秘莫测的“夜先生”,医术通神,面具覆面,面具之下是灭门血仇与......
- 2.2万字1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