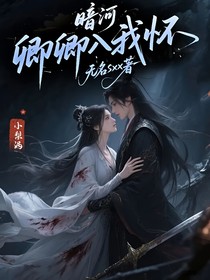番外HE篇 (2-1)
*以电影化的运镜进行改写*
雁门关的荷花开得最盛那日,明砚正佝偻着背,在老墙根下弯腰侍弄新抽的荷茎,布满皱纹的手指在湿润的泥土间细细摸索。忽然,一阵骚动从关口传来,打破了午后的静谧。
“爷爷!爷爷!”明谦像只脱了缰的小马驹,连跑带跳地冲过来,小脸涨得通红,“关口来了队人,说是、说有位姓沈的先生,要见种荷的人!”
明砚直起身,膝盖骨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心头莫名一颤。姓沈?这些年,雁门关鲜少有江南来的沈姓客人。他拄着拐杖,缓缓往关口走去。远处,城楼下站着个青布衫裙的女子,鬓边簪着一支风干的荷梗,正仰头望着那段留着的老墙根,目光深邃如水,仿佛藏着一场漫长的等待。
“老人家可是明砚先生?”女子转过身来,声音清润如潺潺溪流,眼角虽有细纹,却掩不去那份沉静的气质。
明砚愣住了。这眉眼,这神情,分明是记忆深处那个熟悉的沈姑娘,只是少了当年的锐利,多了几分岁月雕琢出的柔和。不等他开口,女子已俯身行了一礼:“在下沈辞,自江南来。”
“沈……沈姑娘?”明砚手中的拐杖“当啷”落地,白发颤巍巍地抖动起来,“不可能……您怎么会……”
沈辞轻笑一声,俯身拾起拐杖递还给他:“当年萧将军送我去江南寻药,本以为回不来了,却在那里遇了位奇人,调养了三十年,总算能再次踏进雁门关。”她停顿片刻,望向不远处的荷田,声音低若耳语,“总想着,要等荷开满关,再来见他。”
话音未落,身后响起沉稳的脚步声。一位身着墨色常服的老者缓步走来,身形不及曾经挺拔,腰杆却依然笔直,鬓角斑白,眉眼中透着温润,正是萧彻。他手中握着一个小小的锦囊,露出半截荷纹佩——与明砚颈间挂着的那枚,竟是一对。
“她总说要等荷开,我便守着这关,守着这荷,等了整整三十年。”萧彻站在沈辞身旁,声音低沉而绵长。两人目光交汇,像是两汪久别重逢的泉,“前几日听说江南来了位爱荷的先生,我便知道,是风把您送回来了。”
原来,当年萧彻并未战死,而是重伤后隐退疗养;沈辞则在江南寻药续命,两人靠着书信维系牵挂,约定待安好之时,在雁门关的荷田重逢。那些未能寄出的字句,那些埋藏心底的情感,终究被时间酿成了圆满。
明谦看得呆住,手里的莲蓬“啪嗒”掉在地上。明砚已是老泪纵横,颤抖着握住两人的手,久久无言,只喃喃重复:“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北狄的小郡主恰巧带着侍女路过,见到这一幕,歪着脑袋问道:“明爷爷,这两位就是唱《荷风谣》里提到的沈姑娘和萧将军吗?”
沈辞蹲下身,轻轻摸了摸她的头,嘴角扬起浅笑:“是啊。”
“那你们会教我唱完整的《荷风谣》吗?”小郡主眼睛亮晶晶的,“我阿爹说,你们的故事,比荷花开得还要好看。”
萧彻朗声大笑,虽然护心镜早已卸下,笑声却仍透着当年的爽朗:“不光教你唱,还要教你种荷。这关的荷,要我们一起守护下去。”
那一日,雁门关的荷风吹得格外浓烈,香气四溢。沈辞和萧彻并肩走在荷田边,她的布裙扫过荷叶,带起串串露珠;他的手指偶尔拂过莲蓬,沾上一点清甜的气息。两人没说太多话,只是静静地走着,像寻常的老夫妻般,将三十年的等待融进每一步的相伴。
明砚目送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忽然发现沈辞鬓边的荷梗多了一片新叶,萧彻的衣角卷着点粉白的花瓣。仿若时光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样。
孩童们的歌声再度响起,仍是那首《荷风谣》,只是调子欢快了些。沈辞轻声哼唱,萧彻侧耳听着,忽然插了一句:“荷风归,故人还,一关风月两心牵。”
风掠过荷田,沙沙作响,好似也在附和。远处的商队停下脚程,北狄的牧民勒住马缰,都笑着望向这片荷田——有些故事无需埋在风里,也无需藏于荷香,它们终会归来,携着岁月的温度,化作雁门关最动人的风景。
江南雪,长安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倾世王妃宠无边
- 男主:谢司珩女主:司遥男二:贺行轩,萧言女二:孟悦悦,洛漓倾世王妃宠无边是一本甜宠文,男主是恋爱脑,也是妻管严
- 1.9万字7个月前
- 如梦令,待君归
- 百年前,仙魔大战,瑾夙仙君下凡渡劫,投身到下修界的仙月派中,如梦令的传闻引发江湖动荡,各门派的弟子为探其真相,共同闯荡江湖的故事。
- 5.0万字4个月前
- 朝心1
- 就是一个师傅和两个徒弟的故事
- 1.9万字3周前
- 绮错一卷
- 天下初定,五国鼎盛。东澜国作为五国之首,与其他四国签订合盟,以联姻为基,化国之争端。此传统延续长达数十年之久。东澜国主之女上官芷雨,为躲避联......
- 0.1万字2周前
- 血刃折
- 简介正在更新
- 2.8万字2周前
- 暗河:卿卿入我怀
- 谢青瑶vs苏昌河1v1原创女主谢家的美人刺vs苏家的寸指剑“双日为昌,意为兴盛、明亮,昌河,意为让暗河走出阴暗,迎来光明。”“他们说谢家隐藏......
- 3.3万字5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