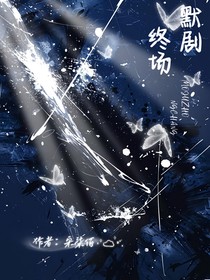番外:循环囚徒009(番外完) (2-1)
我第一次见到季昀时,他正在电梯里整理领带。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三早晨,阳光透过出版社大楼的玻璃幕墙,在他侧脸投下细碎的光斑。他皱着眉头,手指笨拙地摆弄那条深蓝色条纹领带,显然不习惯这种束缚。我站在电梯外,鬼使神差地按下了开门键。
"需要帮忙吗?"我问。
他抬头看我,眼睛在镜片后微微睁大。那一刻,我心脏停跳了一拍,不是比喻,是物理意义上的停跳。有什么东西在我胸腔深处苏醒,像被囚禁千年的困兽突然嗅到了自由的气息。
"谢谢,我自己可以..."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电梯突然剧烈震动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出版社老旧的电梯缆绳断裂前的最后警告。但在那一刻,我的身体先于意识行动起来。我扑进电梯,抓住他的手腕往外拽。他的皮肤很凉,像浸过清晨的露水。
我们摔在走廊地毯上的瞬间,身后传来金属断裂的轰鸣。季昀的眼镜飞了出去,他趴在我胸口,睫毛扫过我的下巴。我闻到他发间淡淡的雪松气息,混合着印刷厂特有的油墨味。
"你救了我。"他说,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
我本该说"不客气"或者"举手之劳"之类的客套话。但当我望进他浅褐色的瞳孔,脱口而出的却是:"这不是第一次。"
因为我在他眼里看见了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往昔——暴雨夜的拥抱,晨光中的亲吻,还有他死在我怀里的七种方式。
第二次循环开始时,我吐得昏天黑地。
记忆像高压水枪般冲进大脑,我跪在浴室瓷砖上,看着呕吐物里夹杂的血丝。镜中的我双眼通红,不是熬夜后的血丝,而是真正的、不自然的猩红。
我想起了一切。
包括最重要的部分:季昀不能活过今天。这是我与死神交易的代价,用我的永恒换他的七日。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杀戮,每一次都要用不同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
第一次我用了注射器。他信任地让我帮他打所谓的"破伤风疫苗",直到瞳孔扩散还在叫我的名字。
第二次是精装版的《草叶集》,书脊砸碎了他的太阳穴。血溅在惠特曼的诗句上,像某种亵渎的注解。
第三次...
我拧开水龙头,把脸埋进冰冷的水流。水珠顺着发梢滴落时,我听见卧室传来动静。季昀醒了,像过去六次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一无所知。
"世诚?"他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柔软,"你起这么早?"
我擦干脸,从医药箱底层取出准备好的手术刀。刀刃在晨光中闪着残忍的光泽。
"来吃早餐。"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平稳得可怕。
第四次循环后,我开始遗忘。
不是关于杀戮的部分,那些细节烙印在骨髓里,清晰得令人作呕。我遗忘的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喜欢在咖啡里加两滴香草精,他左肩有颗痣,他紧张时会无意识咬下唇...
这些碎片从指缝间溜走,像握不住的沙。每次醒来,我都感觉心里有什么被挖走了一块,留下血淋淋的空洞。
到第六次时,我只记得必须杀他。原因已经模糊,只剩下刻进本能的执念。就像现在,我站在地下室,看着棺材里相拥的两具尸体,却想不起我们曾经如何相爱。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死亡。"我对季昀说,声音陌生得像是别人的。
他颤抖的手指抚过棺中尸体交握的手。那具属于"我"的尸体无名指上有圈淡淡的痕迹,像是常年佩戴戒指留下的。我突然头痛欲裂。
"为什么...你会杀我?"季昀问。
记得你终有一死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前任哥!接招吧!!!
- “子纤…你不记得我了…”“什么啊,你是谁啊”根据本人亲身经历改编…结局还未想好
- 0.6万字7个月前
- 她不是恶女
- [也许比狮子勇猛的同时,展现出鸽子羽毛般的温顺。] [我会找出真正的力量,那就是“爱”]自私自利的恶女,在12年前的那场意外下结识了背负杀......
- 3.9万字6个月前
- 风信花之约
- 在命运的无常中,叶无常与林墨璃,两个被病魔折磨的灵魂,在病友交流会上偶然相遇。叶无常,28岁的自由摄影师,用镜头记录生活的点滴;林墨璃,26......
- 2.5万字5个月前
- 我真的很美丽(单纯分享语法)
- 英语语法(适用于初中,高中,专升本和四级的基础语法)
- 10.6万字5个月前
- 海风吹过咖啡馆
- 世界总有人在隐藏着自己的秘密,自己过去的往事,当你遇见那个可以诉说秘密的人时,往事带来的伤口会绽放出夏日最灿烂的玫瑰,林千宴不止一次的看过海......
- 1.5万字1个月前
- 默剧终场
- 双男主。这里有不同的小世界。主角是不同的。因为作者想象力不够。没法把一个小世界写的很长很长
- 6.3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