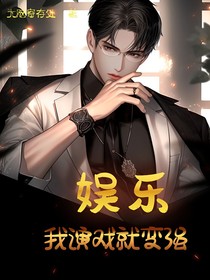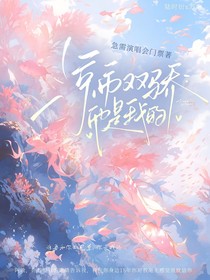第39章 印章里的余温 (3-1)
木盒被林砚之抱在怀里,雨丝顺着伞沿滑下来,在她胸前洇出一小片湿痕,可掌心攥着的青田石印章却透着股细润的暖。她踩着老宅后园的青石板路往回走,脚下的青苔滑得厉害,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像怕惊扰了藏在空气里的、属于顾时谦的气息。
廊下的木椅还在,就是当年她喂三花猫的那把,椅面被岁月磨得发亮,边缘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猫爪痕——是当年那只三花猫调皮时挠的。林砚之把伞靠在廊柱上,抱着木盒坐下,指尖摩挲着印章上的刻痕,“砚之”两个字方方正正,旁边的“时”字略小些,笔画收得极轻,像是怕压疼了旁边的名字。
她忽然想起顾时谦十七岁那年学刻章,蹲在祖父的书房里,握着刻刀的手抖个不停,第一枚章刻得歪歪扭扭,连“时”字的最后一笔都刻断了。他懊恼地把章扔在桌上,说“真难”,她凑过去捡起来,说“好看”,然后偷偷藏在了自己的笔盒里。后来那枚断了笔的章,跟着她从老宅搬到新家,又从新家搬到南方的大学宿舍,直到毕业时整理行李,才发现它被压在箱底,刻痕里积了层薄灰。
“原来你早就在练了。”林砚之对着印章轻声说,指尖顺着“时”字的笔画慢慢划,像是在摸他当年握刀的手。雨停了,天边透出点淡蓝,风穿过银杏树叶,把叶子上的水珠抖落下来,滴在廊下的青石板上,叮咚作响,像他当年刻章时,刻刀落在石头上的声音。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起来,是古籍修复工作室的陈姐发来的消息:“砚之,上次那本明代的《园冶》,页脚的虫蛀处我试着补了补,总觉得不对,你有空来看看吗?”
林砚之攥了攥手里的印章,回复:“我现在就过去。”
她把木盒和印章放进包里,又回头看了眼老宅的后园——银杏树叶在风里晃着,像顾时谦当年笑着朝她挥手的样子。她轻轻说了句“等我回来”,转身走进了巷口。
工作室在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块木牌,写着“拾光古籍修复”,是林砚之亲手写的。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浆糊味和宣纸味扑面而来,陈姐正坐在工作台前,手里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夹着一张薄如蝉翼的补纸。
“你可算来了。”陈姐抬头,看见林砚之,眼睛亮了亮,“你看这里,我用楮树皮纸补的,可颜色总比原纸深一点,怎么调都不对。”
林砚之走过去,俯身看着桌上的《园冶》。书页已经泛黄,页脚被虫蛀出了几个不规则的小洞,陈姐补的地方确实有些突兀。她伸出手指,轻轻摸了摸原纸的质地,又拿起旁边的楮树皮纸,放在鼻尖闻了闻——是新纸,少了点岁月沉淀的陈旧感。
“我记得祖父的书房里,有一沓民国时期的楮树皮纸,颜色和这个差不多。”林砚之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那个木盒,“昨天在老宅找到的,里面除了印章,还有几张纸,我看看是不是。”
她打开木盒,里面果然除了印章,还有一沓叠得整齐的宣纸,纸张颜色偏浅黄,质地柔软,摸起来带着点粗糙的纹理——正是民国时期的楮树皮纸,是祖父当年特意留下来,用来修复古籍的。
“就是这个!”陈姐凑过来,眼睛瞪得圆圆的,“你这丫头,真是藏了宝贝!这种老纸现在可不好找了,用它补,颜色肯定能对上。”
林砚之笑了笑,拿出一张老纸,又从抽屉里取出浆糊——是她按照祖父留下的方子调的,用面粉和水,加了点白芨粉,黏性刚好,还不容易变色。她把浆糊轻轻涂在补纸的边缘,然后用镊子夹起补纸,对准虫蛀的洞口,一点点贴上去,再用干净的毛笔轻轻扫平,动作轻柔得像在抚摸易碎的时光。
断绝关系后,她们悔不当初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娱乐:我演戏就变强
- 林北穿越成横城的包租公,获得戏神系统,拍戏就能获得角色能力。国民女神要住我家和我讨论演技?那我们就深入交流!娱乐圈太子要和我竞争角色?你是太......
- 6.7万字10个月前
- 星际斗争
- 传说中有47位战士。他们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最纯粹的力量。也是吸引无数强大的怪物和人类的记载。
- 2.6万字8个月前
- 灵魂低语
- 在偏见与误解交织的世界里,你是否有勇气直面灵魂深处的自己?《灵魂低语》为你讲述周彤溪的不凡人生。曾为周铜玺的她,因内心性别认同与生理性别冲突......
- 1.1万字8个月前
- 晨昏线I
- “晨昏界”,宇宙核心之地,亦是人族文明的所在地,天澜大陆作为晨昏界中的一片广大区域,被两大势力分块占据:科技兴盛,占地广大的【寻星会】,反抗......
- 3.0万字4个月前
- 京市双骄:他是我的
- 穿越ABo陆时衍x苏喻双豪门+青梅竹马+无条件护短+暗暗占有欲+榆木脑袋—“阿喻我不想和你做兄弟,你能明白吗?”—“陆时衍就算我是omega......
- 1.9万字3个月前
- 九个绝色未婚妻都在等着我离婚
- “三年联姻,叶天然在肖倾城眼中是一无是处的赘婿,离婚当日,她决然将他扫地出门。本以为人生自此黯淡,却不料,九个绝色未婚妻接连现身!职场叱咤的......
- 24.5万字2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