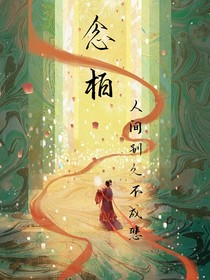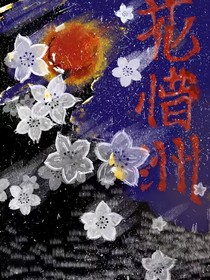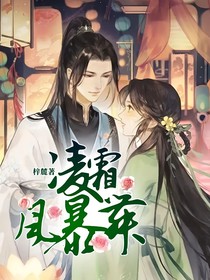第十九章:花影叠山河 (2-1)
寒露的风卷着枯叶,雁初在岭南的渔港码头,见着艘新造的渔船。船帆上绣着大片锦雀花,粉白花瓣间嵌着几粒银亮的花籽,被海风一吹,籽壳碰撞着发出细碎的响,像串流动的风铃。
“这是船家闺女绣的,”补网的老渔翁往网眼里塞了把花籽,“她说花籽在网里藏着,撒网时落进海里,说不定能在岛礁上长出花来。”渔网的绳结上,果然缠着些干枯的花藤,是去年西北商队带来的品种,藤条坚韧,被海水泡了半年仍没朽烂。“商队的人说,这藤能拴住风浪,就像故事能拴住人心。”
渔翁的船舱里,摆着个奇特的陶罐:下半截是岭南的红陶,刻着海浪纹;上半截是西北的灰陶,雕着花藤,接口处用铜箍箍着,箍上刻着“楚”字。“是波斯商人帮忙补的,”他摩挲着陶罐说,“他们说不同的陶能拼出好罐子,不同的花能开出好春天。罐里的淡水,泡着各地的花瓣,喝着都带甜味儿。”
罐底沉着片蓝紫色的花瓣,正是波斯“东方梦”的品种。花瓣旁漂着半片苏州的杏花瓣,像两只相依的蝶。“闺女说,花瓣在水里能说话,岭南的浪涛、西北的风沙、苏州的雨声,都能融进水里。”渔翁倒出些水,水面上果然浮起层细密的泡沫,聚成朵模糊的花形。
离港时,码头上的杂货铺正往木箱里装绣品。掌柜的是个瘸腿汉子,每叠绣帕中间都夹着张花籽纸——用锦雀花瓣捣浆做的纸,透着淡淡的粉,纸上印着行字:“此花来自东方,携善意而行。”“这是发往波斯的货,”他指着帕子角落的小字,“每个帕子都绣着寄件人的地名,苏州的绣‘苏’,京城的绣‘京’,就像给花籽写了封家书。”
木箱的缝隙里,塞着些干枯的花茎,是西北的锦雀花藤,茎秆上还留着被骆驼啃过的齿痕。“商队说这藤能驱虫,”汉子笑着说,“去年有批货被虫蛀了,就这箱因为塞了花藤,半点没坏。你看这藤上的刺,倒像护着花籽的小卫士。”
北行的船过长江时,遇到艘返航的漕船。船工们正用锦雀花瓣熬粥,米香里混着清苦的花香。“这是苏州义仓送来的新米,”领头的船工给雁初盛了碗,粥面上漂着片完整的花瓣,“他们说米里掺花籽,煮出来的粥更养人,就像日子里掺着念想,再苦也有甜。”
漕船的桅杆上,挂着个褪色的锦囊,里面装着半块双鱼佩的拓片——是当年顾言爷爷遗失的那半块,如今被拓在锦雀花纸上,旁边题着行字:“物归原主易,情归原乡难,所幸花记路。”船工说,这是江南的书生题的,“他说佩是死的,花是活的,活花带着死佩的故事走,倒比佩自己记得牢。”
回到京城时,庭院里的菊花开得正盛,花丛中混着几株晚开的锦雀花,花瓣边缘泛着金边,是波斯“东方梦”与中原品种杂交的新花。“萧珩说这花该叫‘合欢’,”锦雀正用新花的花瓣调胭脂,指尖沾着淡淡的粉,“你看这颜色,既有中原的柔,又有西域的艳,像各地的故事融在了一起。”
萧珩的书案上,摊着张新绘的地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着锦雀花的踪迹:粉色是中原,蓝色是西域,黄色是岭南,每个点都用花形符号标注,符号旁注着日期和故事——“江南,绣娘教渔村姑娘绣花,籽落网眼”“西北,学堂用花籽点朱砂,字带花香”“波斯,贵族以花为名,嫁女必绣之”。
“这是给孩子们编的《花路图》,”他指着图边角的小画,是个戴银簪的女子牵着个孩子,孩子手里的种子正落在地上,“让他们知道,花走的路,就是人心里的路。”图的空白处,贴着片岭南的茉莉花瓣,与苏州的杏花、波斯的蓝瓣挤在一处,像群凑趣的小生灵。
锦雀归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所谓你知我意
- 孤音国和残月国一向不睦,传闻孤音国有一位年纪轻轻英姿飒爽的女将军,她带领自己的国家一次次取得胜利,也有许多人想至她于死地。 这日......
- 1.2万字7个月前
- 白月梵星:何以生欢
- 都说四大妖王里,皓月殿殿主·极域妖王梵樾:狂妄自大,霸道凶狠。而冷泉宫宫主·瑱宇:心狠手辣,冷情冷血。星芒阙阙主·棠欢:不喜争斗,来无影去无......
- 0.2万字6个月前
- 念柏—人间别久不成悲
-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 15.1万字5个月前
- 花惜洲
- 简介正在更新
- 0.7万字5个月前
- 倾世疯魔
- 大梁朝的京都,盛世繁华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疯批美人叶倾歌。她出身名门叶府,容貌倾城,才情无双,本应一生荣耀。然而,一场家族......
- 1.0万字4个月前
- 凌霜风暴舞
- 沈家大小姐与纨绔子弟的故事
- 1.5万字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