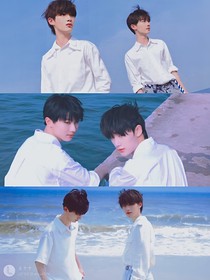第84章 杏林盟动,暗战将启! (2-1)
回到京城第二日,我在王府西侧跨院的耳房里支起了炭盆。
阿铁搓着冻红的手哈气,小翠花把药箱往八仙桌上一放,铜锁"咔嗒"撞出脆响:"沈姑娘,您说要商量大事,是不是要开分店了?"
我掀开棉帘,看见萧凛抱着一摞文书站在廊下。
他素日总穿玄色锦袍,今儿换了件月白夹袄,倒像个来听先生讲学的贵家公子。
见我望过去,他屈指叩了叩门框:"我在偏厅等。"话音未落,人已转了弯。
"咳。"我坐回椅子,把炭盆往阿铁脚边推了推,"不是开分店,是要办件大事。"阿铁的粗布袖管蹭过桌沿,带倒了茶碗,"哗啦"溅湿半张宣纸。"影蛇的人在暗,我们在明。"我盯着他慌忙擦桌子的手,"我需要你们联络江湖上的游医、药农、走方郎中——他们走南闯北,见的多,听的也多。"
小翠花忽然把脸凑过来,她鬓边的红绒花扫过我手背:"您是要我们当...探子?"
"是耳目。"我握住她的手,她掌心有常年握药杵磨出的茧,"上个月在云州,有个卖草药的老伯跟我说,山脚下有帮人半夜挖地洞。
后来才知道,那是影蛇在埋火药。"我抽回手,指节敲了敲桌案,"以后你们听见什么不对劲的,比如突然多了外地口音的药商,或者哪家医馆平白无故关门,哪怕是村头老妇说夜里有狼嚎——都记下来,让秋月传给我。"
阿铁的喉结动了动:"沈姑娘信得过我们?"
"信。"我从袖中摸出三枚刻着杏林图的青铜令牌,"这是'杏林盟'的信物。
见到令牌的人,都是自己人。"令牌落在桌上,发出清响。
小翠花立刻捡起来,用袖子擦了又擦:"我明日就去城南药市,找刘婶子她儿子,那小子跟着商队跑漠北,准能打听到消息。"
阿铁一拍大腿:"我去联络城西的老周头!
他在大牢里给犯人治过伤,认识的三教九流多着呢!"
我望着他们发亮的眼睛,喉咙突然发紧。
前世在急诊室,我总觉得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可现在才明白,在这吃人的世道里,护住更多人的命,有时候得先拆穿吃人的鬼。
"都收着。"我把最后一枚令牌推给阿铁,"后日义诊开棚,你们就以医馆伙计的身份走动。"
第二日卯时三刻,我站在医馆门口,望着青石板路上逐渐聚起的人群。
冬风卷着药香混着汗味扑过来,有妇人抱着发烧的孩子挤过来,有老汉拄着拐杖喊"沈大夫",还有穿粗布短打的汉子举着药罐子问:"您说的治冻疮的方子,当真只要辣椒秆煮水?"
"当真。"我笑着应,眼角余光却扫到街角。
那穿月白棉袍的男子站在糖葫芦摊边,脚尖无意识地碾着碎冰——他明明裹得严实,额头却渗着细汗,右手始终攥着左袖。
"这位郎君,可是哪里不适?"我穿过人群,虚扶他胳膊往医案引。
他袖中硬物硌了我手背一下,是匕首柄的弧度。
"胃...胃里胀。"他喉结上下动,"前日吃了冷炊饼。"
我搭住他手腕,脉跳得像擂鼓。"伸出舌头我瞧瞧。"趁他张嘴时,我指尖快速点了他"内关""合谷"两穴。
他瞳孔骤缩,刚要喊,我另一只手已扣住他后颈:"影蛇的人,装病也该学个像样的——胃胀气的人舌苔该是白腻,你这舌尖红得像染了朱砂,分明是急火攻心。"
"你...你胡说!"他挣扎着要掀翻医案,药碗"噼里啪啦"砸在地上。
秋月带着两个护院从后堂冲出来,绳子"刷"地套住他手腕。
我扯住他左袖一拽,三寸长的匕首"当啷"落地,刀刃泛着青黑——淬了毒。
冷宫弃妃?王爷读心后独宠我一人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重生之:我在快穿当顶流
- 醒来发现不在原来的世界了,身边还有一个超级大帅哥?还让我离婚,这不然不可能啊……
- 0.7万字6个月前
- 青山见海
- 穿书后的顾竹青认为,她应当拯救苍生,或者嫡女复仇,还有炮灰逆袭...!系统101:...不好意思,您的任务是攻略反派...楚野。某人默默吐了......
- 1.3万字6个月前
- 月和星不善言辞
- 番茄同名,有人看再更兴帝国由于疆土过于庞大,全国62亿的人囗,中央必须把权力分出去,于是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大通政和大祭司替代兴神管理大地,但这......
- 3.4万字5个月前
- 你似繁星入我生
- 穿越
- 14.0万字4个月前
- 快穿,反派的小甜心
- 男女主双洁,小甜饼,女主汐宁孤儿,在原世界磕磕绊绊长大,一场意外,被系统绑定,踏上了拯救反派的道路。目前更新界面:你知道我吗?自卑敏感校霸X......
- 2.7万字11小时前
- 穿越之我是狐狸??!
- 嗯……不透篇哈
- 0.3万字8小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