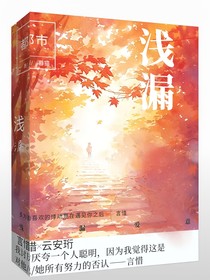就让我替你完成这个心愿 (2-1)
八年后的深秋,巴黎卢浮宫的玻璃穹顶正漏下最后一缕金红的晚霞,斜斜落在《未完成的自画像》的画框上。我站在画前,指尖隔着防尘玻璃,一寸寸描摹画中少年的轮廓——楠瑾的睫毛在画布上投出细碎的阴影,像极了那年桂树下,碎金似的阳光落在他睫毛上的模样。他穿着高中时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袖口卷到小臂,腕骨处有一道浅浅的疤,那是他给我绣桂花裤子时,被针扎出的旧伤。
画里的他正坐在桂树下,膝头摊着一本素描本,笔尖悬在纸面三毫米处,仿佛下一秒就要落下。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槐树叶,在他发梢跳跃,耳后还沾着一点没擦干净的铅笔灰——十七岁那天,他就是这样蹲在树下,用手语比划着“我想当画家”,指尖在空气中划过弧线,铅笔灰蹭得耳廓发灰,眼里的光比头顶的太阳还要亮。
这幅画展出三个月,已经成了艺术圈绕不开的话题。评论家在专栏里写“画中少年的沉默里藏着海啸般的深情”,收藏家们为它拍出八千万欧元的天价,连塞纳河畔的街头艺人都在临摹它。可只有我知道,画里那束光的角度,是楠瑾教我的;素描本边缘故意磨出的毛边,是他当年总爱用指甲刮纸页的习惯;甚至他唇角那抹若有若无的笑意,都复刻了他第一次给我看素描本时的模样——那时他刚画完我啃冰棍的侧脸,笔尖还沾着奶渍般的白色颜料。
展厅的人潮渐渐散去,暮色漫过《蒙娜丽莎》的微笑,漫到我脚边。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经纪人发来的消息:“威尼斯双年展确认《守护者》作为压轴作品,开幕式定在下月十五号。”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光标,忽然闻到一阵若有似无的槐花香,像极了那年夏天,陈砚栽进粪坑后爬上来时,身上混着臭味的清甜。
八年前的暴雨天,楠瑾的葬礼刚结束一周。我撬开他房间里那上了锁的柜子,后来在锈盒子的最底部诊断书上看到“肺癌晚期”四个字时,才突然明白,那是他咳的血。毛衣里裹着张便签,是他用左手写的,字迹像被狂风揉过,墨痕洇了又洇:“等你成了画家,就把我的画挂在你旁边。”
那天我抱着毛衣在空荡的房间里坐了整夜。十七岁的楠瑾突然在记忆里变得异常清晰:他半个身子浸在粪坑里,却死死把我护在身后,污水顺着他的蓝衬衫往下滴,像开了片灰败的花;他发着高烧冲我笑,手指在被子底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却坚持要把热水袋塞给我;他给我绣桂花裤子时,扎破的手指在布上洇出小小的血点,却咧着嘴比划“这样更像真花”。
第二天清晨,雨停了。我收拾好他留下的素描本,搬了把小板凳坐在桂树下。树影落在画纸上,像他当年为我挡过的阳光。我试着画他栽进粪坑那天的样子,铅笔在纸上沙沙地跑,忽然明白他为什么总在素描本上写我的名字——原来喜欢一个人,连笔尖都会不听话,会下意识地追着那个人的影子跑。
往后的八年,我像活在他的影子里。他的素描本被我翻得卷了边,每一页都写满批注:“这里的光影应该再暖些,像他揣在怀里的热水袋”“跳皮筋时的裙摆弧度要更软,他说过像白蝴蝶停在花上”“哭的时候肩膀抽动的幅度要小一点,他总说我哭起来像只受了委屈的小猫”。有次画到他护着我对峙那群人的场景,颜料调得太暗,眼泪滴在画布上,晕开一片灰蓝——像极了他送我的那条裤子的颜色。
成名后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我在纽约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办展,在东京的森美术馆开讲座,可每次站在聚光灯下,总觉得楠瑾就站在人群里,穿着那件蓝衬衫,冲我比划“真棒”。有次记者追问:“您的画里总藏着一种未说出口的遗憾,是在纪念什么人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突然发抖,眼前闪过他那本泛黄的手语书,“我爱你”那页的折痕深得能塞进整个青春。
对不起楠瑾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浅漏
- 当持续三年的暗恋迟迟未得到回应,相逢后又应当如何收场呢一天码1500~3000字左右。打赏可催更(五千字)十朵玫瑰花更新两千字作品底下评论作......
- 0.3万字7个月前
- 我的alpha哥哥
- 哥哥与弟弟
- 2.1万字6个月前
- 蜂拥
- 登机广播响起,我正在货架间寻找最后一盒口香糖。防撞条上的污渍拼出半个音阶,这个瞬间我突然听懂了她常哼的《游牧人》——那些摩尔斯电码般的节拍,......
- 2.3万字5个月前
- 捡个兽人回家当老婆
- AB0双男主
- 0.2万字4个月前
- 埋藏在阴谋中的爱
- 来自阴谋中的爱意,在这个世界的法则中,每个人都心怀鬼胎,没有人能猜到对方是否骗了自己,是否埋藏着阴谋
- 1.7万字1周前
- 奕夏终长明
- 这是一个青春伤痛小说框架,融合了青涩的初恋、现实的碰撞与深刻的遗憾这个结局是彻头彻尾的悲剧,没有反转,没有奇迹。它的力量在于展现生命无常、爱......
- 1.3万字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