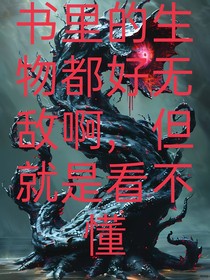第八章沦陷 (9-5)
夕阳把西部战线的烟尘染成铁锈色,撤退的队列像条断裂的蛇,在废墟间蜿蜒向东。特解部队的装甲车碾过战友的遗体,车顶上的机枪手望着后视镜——那些穿着同色军装的身影正被潮水般的感染者吞没,最后一声呐喊混在尸群的嘶吼里,碎得听不清。
全员覆没……通讯器里传来沙哑的报告,随即被炮声切断。炮兵部队正拖着炮管往东侧高地转移,炮口在颠簸中不断指向身后的防线。首轮齐射炸开时,西边的天空猛地亮了,燃烧的断墙把撤离士兵的影子钉在地上,像一排来不及拔起的墓碑。
有人回头看了眼,被特解队长狠狠按下:别看!跑!靴底溅起的碎石里混着滚烫的弹片,那是刚从西线飞过来的礼物。
北线的运输机正在低空盘旋,绳梯垂在断楼之间,难民们互相推搡着往上爬。机枪手跪在楼顶边缘,对着围过来的感染者泼洒子弹,枪管烫得能煎鸡蛋。最后一架!快!他嘶吼着,突然被一只感染者扑中,连人带枪坠下楼顶,坠落的瞬间,他看见运输机的尾翼已经转向东方。
西线的炮声还在持续,像在给牺牲的一线部队送行。撤离的队伍里没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喘息声,在炮轰的间隙里显得格外清晰。有人的背包里掉出张照片,被风吹着滚向西方——那是西部防线完好时,整支部队在炮位前的合影,如今照片上的人,只剩一半还在向东移动。
夜幕降临时,炮兵阵地在东侧高地架好了炮。最后一轮齐射覆盖了西线的必经之路,火光中,隐约能看见一线部队最后据守的碉堡正在坍塌。特解队长摘下头盔,对着西边的方向敬了个礼,转身时,发现北线撤离的运输机正从头顶飞过,机舱灯在黑暗里像颗摇摇欲坠的星。
军港北部战线
船员:舰长,我们已到达北部战线。
德尔文:听着,你的任务是坚守此地3小时。为后方难民撤退争取时间。
船员:保证完成任务!
德尔文:……保重。
铁丝网在撞击声中剧烈摇晃,最前排的感染者已经能看清脸——那个穿着破洞作训服的士兵,胸前还别着半个被血浸透的编号牌,正是三天前负责弹药补给的列兵;旁边挤着个抱着婴儿的难民,孩子早已没了声息,她却仍保持着托举的姿势,指甲在铁丝网上刮出刺耳的声响;还有个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安全帽下露出半边溃烂的脸,手里攥着的扳手每晃一下,就溅出几滴黑血。
阵地里的新兵突然干呕起来,他认出那工人是昨天帮他们修过工事的老周。班长一脚踹在他腿弯:“打!打偏一点就等着被拖下去啃!”重机枪的轰鸣立刻盖过了一切,子弹在尸群里犁出扇形的血沟,却挡不住后面的人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爬。
有个穿军官制服的感染者卡在了铁丝网缝隙里,肩章上的星徽还闪着微光,他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气音,眼睛死死盯着阵地中央的军旗——那曾是他亲手升起的旗帜。新兵的枪口抖了一下,对方突然猛地往前一挣,带刺的铁丝瞬间贯穿了胸膛,却离阵地又近了半米。
“它们记不住自己是谁了,”老兵往冲锋枪里压着弹匣,声音发哑,“但这身皮、这地方,还刻在它们骨子里。”尸群已经压到了阵地前沿,有士兵被一只从地下钻出的感染者拖进了战壕,惨叫声很快变成模糊的咀嚼声。
阳光突然被尸群挡住,阵地陷入短暂的阴影。幸存者们背靠背站着,枪膛发烫,视线所及之处,全是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他们曾一起敬礼、一起排队领过罐头、一起在工棚里喝过劣质烧酒,而现在,只能用子弹来“送别”。
子弹在尸群里溅起血花,却像打在湿麻袋上——被打断胳膊的感染者依旧用另一只手往前爬,断腿的则像条蛆虫,在地上扭出蜿蜒的血痕。有新兵慌了神,对着躯干疯狂扫射,直到班长拽过他的枪管,狠狠砸向最近一个感染者的太阳穴:打头!看清楚了再打!
零号行动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规则怪谈:光头强疯了(同人)
- 方老六,你的朋友田老七被传送到了怪谈世界,《光头强疯了》他将扮演李老板,在光头强家里住上两个夜晚,请帮助他生存下去。
- 1.0万字7个月前
- 从铠甲的全片场走过
- 星耀征途:跨次元的铠甲羁绊张凌枢,那个心怀浩瀚宇宙梦的高中生,自雨夜邂逅坠落后山的星御帝铠召唤器,命运的齿轮便开始疯狂转动。初次触碰,神秘蓝......
- 3.7万字6个月前
- 供奉殿:小兔子别想逃跑了
- 穿成小舞,还被光翎带回了供奉殿,和发生什么用趣的事情
- 0.9万字6个月前
- 书里的生物都好无敌啊,但就是看不懂
- 阿巴阿巴阿巴
- 36.8万字6个月前
- 人在铠甲,从光影开始的传奇
- 12.2万字5个月前
- 佩恩的异世界之旅
- 天道佩恩因意外穿越到拥有魔法的异世界……
- 0.7万字3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