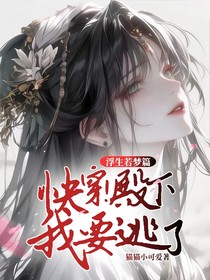第十七章 (2-1)
念荷第一次踏上雁门关的土地时,正是盛夏。
风沙卷着热浪扑面而来,打在他的青布长衫上,带着股粗粝的疼。他背着母亲留下的旧书箱,箱子角磕掉了块漆,露出里面的木纹——那是母亲亲手为他打的,说要让他带着江南的墨香,去看看雁门关的荷。
“后生,找啥呢?”守关的老兵叼着旱烟,看着他在废墟旁打转。那片曾是沈姑娘破屋的地方,如今只剩半截土墙,墙根处长着丛野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我找一片荷。”念荷抹了把汗,声音带着江南口音的软,“我娘说,这里种过荷,黄颜色的,花瓣像柳叶。”
老兵“哦”了一声,吐出个烟圈:“你说的是沈姑娘种的那株吧?早枯了。前几年倒是有个书生来种过一片,可惜冬天一冻,全死了。”
念荷没说话,从书箱里掏出个瓦罐,里面是晚香楼荷塘的藕种,用江南的淤泥裹着,还带着点湿润的水汽。他蹲在土墙根,用手刨开沙土——土里混着点炭屑,大概是当年破屋烧毁时留下的。
“江南的藕,在这儿活不成。”老兵蹲在他旁边,看着他笨拙地埋藕种,“沈姑娘当年埋了五年,也就开了一朵,还是歪歪扭扭的。”
“我娘说,心诚就能活。”念荷的手指被沙砾磨出了血,他却像没察觉,小心翼翼地把藕种埋好,又从书箱里拿出个水壶,倒出里面的水——是他特意从江南带来的荷塘水,带着点淡淡的绿。
老兵笑了,没再劝。他想起沈姑娘当年,也是这样,每天搬着瓦盆晒太阳,雪天里还把棉袄脱下来裹着根,像护着个宝贝。
念荷在雁门关住了下来,就住在关口旁的驿站里。他不像别的书生,总捧着书本看,倒是天天往土墙根跑,松土、浇水,对着刚冒头的绿芽说话。
“今日江南的荷该开了。”
“我娘说,您当年总盼着有人来,我来了。”
“萧将军,我娘让我告诉您,沈姑娘没怪您。”
驿站的掌柜觉得他有点疯,背地里跟老兵念叨:“这书生怕不是读书读傻了?对着几根草说话。”
老兵摇摇头:“他不是傻,是在替人圆梦呢。”
入秋时,土墙根的荷竟真的抽出了茎,顶着圆圆的叶,在风沙里慢慢舒展开。念荷高兴坏了,跑遍了整个雁门关,买了个最大的瓦盆,把荷移进去,摆在驿站的窗台上。
他给江南写信,说:“雁门关的荷活了,叶子比江南的小,却硬挺,风沙吹不动。”
回信很快就来了,是他媳妇写的,说儿子刚会走路,学会的第一个词是“荷”,还说晚香楼的荷塘还在,只是看荷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夫君,早点回来。”信末画着个笑脸,“我和孩子在荷塘边等你。”
念荷把信折好,夹在母亲留下的那本《残荷记》里。那是本手抄的册子,里面记着沈姑娘的事,是赵副将晚年时写的,最后一页画着朵荷花,旁边题着:“荷生江南,枯于漠北,然其香,逾千里。”
入冬前,荷开了。不是黄的,是淡淡的粉,像极了江南的颜色。花瓣虽小,却开得周正,在夕阳下泛着光,引来几只蜜蜂——雁门关的冬天来得早,蜜蜂早就该冬眠了,不知怎的,竟绕着花飞了两圈。
念荷摘下片花瓣,夹在给媳妇的信里,又把那枚荷纹佩——是赵副将临终前托人转交的,说让他还给沈家后人——放在花盆边。玉佩在夕阳下闪着光,背面的“辞”字,像在微微发烫。
江南雪,长安城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
相关小说
- 江南情缘之晚风微雨问海棠
- 苏瑶妹妹苏婉儿沈瑶妹妹沈昭昭沈昭昭义兄沈策沈瑶亲哥哥沈昭昭沈家养女三小姐苏婉儿苏家二小姐大小姐苏瑶江南才女古代豪门千金言情宫廷武林江湖才子佳......
- 3.0万字6个月前
- 艾玛!咸鱼就是好!越来越咸!
- 简介正在更新
- 0.2万字6个月前
- 黎屿
- 当皇兄和弟媳同时重生,狠心渣男是否还会如愿以偿登上皇位?且看黎屿,前世今生的爱恨情仇,请诸位静等小星娓娓道来!
- 0.9万字6个月前
- 落笔弥柔
- 司徒巍大抵从未想过会在满目苍凉中瞥见一抹亮色。只一眼,此生难忘。【这是一个霸道将军爱上清冷(表面上)大夫从而踏上漫漫追妻路的俗套故事。】(啊......
- 0.4万字6个月前
- 穿越之攻略反派BE手册
- 穿越进古代小说,攻略反派
- 4.5万字6个月前
- 浮生若梦篇:快穿!殿下,我要逃了
- 【虐文】【高冷男主与可爱女主的cp】这部小说以一个现代女孩穿越虚拟王国开始攻略男主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他们的爱恨纠葛,对于命运的无奈以及相互......
- 3.2万字5个月前